 艾琳艾德勒(艾琳艾德勒) 艾琳艾德勒(艾琳艾德勒)
|
|
|
1 楼:
[系列翻译]我和福尔摩斯的早年岁月(...
|
04年01月31日17点33分 |
我的早年岁月
当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去世了。
但亲爱的读者,请不要为我悲伤,因为我的一生是那样的充实,我所经历的冒险又是那样的多。
应我的好朋友华生医生的要求,我写了这个关于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早期生活的故事。作为我的丈夫的私人传记作者,或者说,至少是他所经办案件的记录者,曾经参与我丈夫多年工作的华生医生认为,公众有可能对我和他共同度过的早年生涯同样深感兴趣,也会想要知道歇洛克·福尔摩斯是如何学会那些小小的推理伎俩的。
这份手稿,连同其他我有幸参与侦破的案件的记录,在我们去世前,都将被锁起来。在这一点上,歇洛克尤其坚持,因此华生只好勉强同意在我们身前决不发表他们。而众所周知,由于多种原因,歇洛克厌恶在公众中扬名,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对于这部手稿的问世,他还是很高兴的。他不仅读完了它,而且对于他的出版给予了最大的祝福——当然,是在我们都去世后。
现在,我不再需要为了我自己的安宁而假扮一个老处女了。我必须回到我原来的身份——艾米莉·福尔摩斯,而在我结婚前,我叫做——艾米莉·莫里亚蒂。当然,我的父亲,就像你们知道的一样,正是在华生医生写的《最后一案》中去世的莫里亚蒂教授。
但是,在我早年的生活中,我的父亲确实是一个好男人、一个好父亲,而在数学领域里,他毫无疑问更是一个天才。
1857年,我生于伦敦。那时我父亲正在伦敦一所大学教书。而我的母亲,伊丽莎白,是一个才华出众、敏锐而善于说话的女性,我的父亲非常地爱她。作为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我的父亲极其溺爱我。当我七岁时,我母亲再一次怀孕了,父亲当然喜出望外。
然而,那个孩子——一个男孩——还是夭折了,而我母亲也死于难产,留下了我父亲和我在这世上相依为命。
就像许多男人在遭遇到这样的悲伤和痛苦的时候常会做的那样,我的父亲开始更加投入地工作,并借着教育我来逃离这种痛苦。虽然他从来不说,但是我知道他想要一个男孩。在这样的发现后不久,我便设法成为了他的“儿子”。由于拥有数学背景,在教我时,父亲倾向于用一种带分析性的、有逻辑性的方式。
我是一个有着天才头脑的孩子,因此,我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吸收着这些知识。在那个时代,很少有女子,或者容许我斗胆说,即使是在现在的女子中,也没有在学习中得到这样好的教育的。在教我时,父亲从来不把我当成一个女孩,反而把我看作一个迫切需要头脑训练的人。他从来不理会这些课程是否超出了我能接受的范围。而这样的训练的结果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学到了许多同龄的女孩子从来不曾接触到的知识,这些知识也是和我一样的大的男孩子成年之后才学的到的。
父亲总是说,对于我的年龄来说,我太成熟了。问题是,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要这样教育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教育会最终导致什么。
1865年父亲还在伦敦教书的时候,曾经写了一篇论述牛顿第二定律的论文。这篇论文为他在 赢得了一个数学教授的职务。那是我只有八岁。我们离开了伦敦阴郁的生活以及那失去母亲的痛苦回忆,来到了宁静的乡村。我和父亲在一个离开 Credit ion大约五英里,叫做Exeter的地方定居了下来。我们最近的邻居就是的福尔摩斯一家人。由于我在伦敦被认为是一个古怪的人而几乎没有朋友,所以我很期待和福尔摩斯家的两个男孩见面,尽管他们要比我大。而据我所知,我在这里将不会被当作一个怪人来看待——因为这两个男孩子有着和我一样敏锐的头脑。
就在那个命中注定的晚上,我见到了他们。
当我在图书室读书的时候,父亲把他们引了进来。
“这是我的女儿,艾米莉。”教授说道。
我从手上的大部书中抬起头来,快速地看了他们一眼。
“迈克罗伏特·福尔摩斯,和歇洛克·福尔摩斯?”
他们显然被我的推理惊住了,尤其他们面前的不过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我向你们保证,这一点也不神秘。曾经有人告诉我,在这个地区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只有两个,就是Sherri ford Grange的西格森和维奥蕾特夫妇的两个儿子。据说他们之间相差7岁,那正是我从你们身上看到的年龄差距。歇洛克正在伊顿公学就学,而迈克罗伏特——你刚开始在牛津大学的学业。你们的外衣透露了你们就读的令人尊敬的学校的名字。你们这次回来是为了圣诞假期——因为你们还穿着它们。还有,我已经见过了你们的父母——我看的出,迈克罗伏特像爸爸,而歇洛克,像妈妈。”
“当你解释完,现在这看上去很简单了。”迈克罗伏特·福尔摩斯说。
“你能教我们做这些吗?”歇洛克·福尔摩斯问道。
“那取决于你们对于观察的敏锐程度,”我说,“不过我可以试试。”
“请你克制自己,不要那么做,艾米莉,”我父亲说,“没人会喜欢一个忙人。”
“我父亲并不完全欣赏我消磨时光的方式。父亲,我不是一个忙碌的人,我从不传播谣言,我只是预言事实。”
“社区里有一个狡猾的人就够了,”父亲边走出图书馆边说。他并不赞成我所玩弄的那些观察和推理的“游戏”。父亲拥有这样的出众的能力,但是他认为我把它应用得太荒唐了。然而我坚持在人们告诉你某些事情前就把他们掌握了。
迈克罗伏特做得非常好,但是最先却对这样做的目的无所谓,他只关心如何用自己的才智和聪明使别人惊讶。歇洛克显然也有这类实际操作的技能的天赋。
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要教自己这样的技巧。
“我希望成为一名侦探。”我说。
“你的意思是像爱伦·坡笔下的杜宾?”
“比他厉害。”
“一个女侦探?我得祝你好运。”
“我知道最初这看上去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会做的最好。”
“不过这些观察的技巧要怎么帮助你成为一名侦探?”
“他让你时刻保持警觉。头脑和刀不一样,刀一直在使用,而头脑只有在不停解决难题的过程中才能保持犀利。一个人越是经常的观察事物,那么事物对于他就越是明显。”
“为什么对于事物的观察很重要?”
“我相信在很多情况下,对于事物的观察能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具体的说?”
“好吧,”我说,试着找出一个适合的例子,“假如你正在调查一个谋杀现场。你注意到了某种外国雪茄的烟头。如果你知道一些关于雪茄的事情,你就有可能确定它是一种来自Munich的雪茄,但是很少被进口。那说明了什么?”
“那个凶手是德国人?”他问道。
“有可能。除非被害者是个德国人。然后你注意到了桌上的蜡烛忽明忽暗,像要熄灭,然而你到的时候窗却已经紧紧关上。那暗示了什么?”
“窗曾经开过,但另有人在凶杀之后把他关上了。”
“谁?”
“恩,当然不是被害者,而凶手不是从窗进来就是从窗出去的。屋里有另外一个人?”
“完全正确。所以我们现在得找一个同谋了。你看,这就是那些细小琐碎的事物如何使正确的结果浮
“告诉我自行车走的是哪条路?”我问。
歇洛克研究了地面大约几秒钟,“如果地面不是平的,“他回答,”上山的痕迹要比下山的浅。“
“非常好!“我说道,”真的非常好。你正变得非常出色,歇洛克。”
“谢谢你,我亲爱的。”
歇洛克、迈克罗夫特和我常常结伴去EXETER,不仅因为我要买东西,更是测试他们是不是能运用他们学习的推理演绎法在一瞥之下说出一个人的经历或职业。
“那个男的?”我手一指。
“他是个管道工。”歇洛克回答。
“他呢?”
“律师?”歇洛克问。
迈克罗夫特摇了摇头,“法务官。”
“那个女的呢?”
没有人回答我。
我停下了脚步,他们也停下了——因为我一手挽了一个。
“她是一个助产士。”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只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在男人身上,那么,你们就失去了许多可能。”
说完我们继续上路。
“我不懂女人。”迈克罗夫特说。
“我也不懂。”歇洛克说。
“你们不用懂她们,只要推理就可以了。我也不懂她们,但那并不能阻止我。不要让你个人的情感遮盖你的观察能力。”
“你说什么?你的意思是,你不懂女人?!”迈克罗夫特说,“你是其中之一!”
“从性别而言,是。从态度和想法而言,不。”
“我同意,”歇洛克说道,“你令人难以分类。”
“那当然。”迈克罗夫特说。
“我会把那作为一种赞美。”我耸耸肩。
当我在一个学校放假的日子看见歇洛克十,他的脸上有个黑眼圈。
“你的眼睛怎么了?”我问。
“我想对任何人来说这都很明显,尤其是你。有人打了它。”
“我知道那个。我的意思是谁,在什么情况下。”
“一个比我的大的男孩,叫斯盖司。他看我不顺眼。”
“你看上怎么不顺眼啦?”
“我觉得没有。我总想我看上去令人愉快。”
“你的确是。”
我们都笑了,脸也有些红了。
“这事每天都发生吗?”
他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噢,你说这个吗?不——一周一次。他只是一个暴力分子,用不了几年他就会离开学校的。”
“几年?到那时你该有了多少个黑眼圈?”
“让我们算算:三年,每年52星期,扣除假期的6星期……”
“歇洛克!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总共是108个黑眼圈或者更多。我想我能对付。”
“歇洛克!”
“我认真着呢。上校正准备教我拳击。”
“那真的是个好主意吗?平时他不借着上课的理由就经常打你了!”
“或许我会学着保护自己。”
歇洛克从屋里叫着跑向我,“艾米莉!我做到了!我彻底打败了他!”
“谁?斯盖司?”
“噢,他,是的,不,我的意思是上校!”
我大笑起来,“歇洛克,你没有!”
“我有。这滋味太棒了!他要好几天带着黑眼圈了。”
“他说了什么?”我问。
“沉默了几秒钟——他吓到了!但当他清醒过来,他摇着头对我说,‘歇洛克,我想我们找到了你可以做好的事情。”
在教授了我的学生一段时间后,我打算为自己做一些准备,尤其是让自己能充分地观察事物。
“迈克罗夫特,我想你已经证明了你对于报纸杂志的观察力。歇洛克,让我们来看看从上次到现在你学了多少。这是什么报纸?”我举起一篇被小心剪下的文章。
“当然是《泰晤士报》”歇洛克立即回答道。
我点了点头。
“这个呢?”我递个给他一份相似的文章。
“St. James Gazette,”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再次点头。
“这个呢?”
“《西部晨报》?”他想了一会,问。
“不,歇洛克,”迈克罗夫特打断了他,“很显然这是《利滋报》。”
“迈克罗夫特是对的。”我说。
“噢!“歇洛克咒道。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细微的,歇洛克,”我说,“但如果你再多学点就不会犯那样的错了。”
他沮丧地把头往桌子边沿敲。
“也许今天我们学的差不多了。时间也不早了。”
“今晚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参加。”迈克罗夫特说着,起身走向图书馆的大门。
“晚安,艾米莉。”他向我的方向挥了挥手。
“晚安,迈克罗付特。”我回应道,转向歇洛克,“你不打算和你哥哥一起回家了吗,歇洛克?”
“我从来不想学这些。”他说道,一边起身,“学会辨认报纸有什么用?”
“对于报纸的辨认是犯罪学领域专家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的一种。”我说,“你不会了解这知识有多么重要直到有天你需要它们却并不掌握。”
他转动着他纯澈的眼睛,看着我。
“需要我提醒你么,歇洛克,是你,你知道要求我教授这些课程的,不是我自觉提供的。”
“不,你不需要提醒我,”他说,再次跌回他的椅子,“你还有其他关于我学习的意见吗?”
“我只提过的唯一意见,那就是——”
“观察和记忆,”他接下我的话,“是的,我知道。”
“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有按照我的意见去做?”
没有回答。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吐出来。他安静地站了起来,穿上他的外套,慎重地走出了房间。
我想,我伤到他了。我并不是故意去激怒他。我以为他会回答我,用他一贯的敏捷,因为平时我们经常互相取笑。
但这次他什么也没有说。
我茫然地站了好一会,直到我父亲走了进来。
“你的学生都走了吗?”他问。
“是的。”
“出什么事了,艾米莉?”
“歇洛克。”那是我所能说的唯一词语。
“他怎么了?”
“我不肯定。”
“艾米莉,你可以告诉你的老父亲一切。”
我叹气,“有些东西变了,父亲。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真的有东西在我们之间,改变了。”
“那男孩爱上你了,艾米莉。”
“太荒谬了,父亲。那是不可能的。”
“真的吗?”
“当然。他……怎么可能……一夜之间……爱上我?”
“不止一个晚上。你认识他整整五年了。”
“他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过。”
“你是不是教了他们一节特别难的课?”
“不,只是辨认报纸。歇洛克显得异常的吃力。”
“而迈克罗付特,我想,做的更好?”
“他总是做的更好。”
“那么歇洛克吃醋了。”
“怎么会呢?在这些方面,迈克罗付特总是比他更敏锐。为什么歇洛克要让这影响自己?而且这么突然吗?”
“歇洛克在怕他的哥哥。由于他出众的才华,迈克罗付特会偷走他爱的女孩。”
“那太愚蠢了。对于迈克罗付特我能想什么?他比我大10岁。”
“但歇洛克问他自己,‘艾米莉会怎么想我呢……两兄弟里笨拙的那个……’”
“你真的这么认为?”
“我知道他这么想。”
我大笑:“难道他和你讨论过吗?”
“就像讨论过一样。他总是没完没了地讲你,我也亲眼看他对于在你的课上输给迈克罗夫特所表现的沮丧。歇洛克是真的害怕把你输给他的哥哥。”
“那太傻了。他永远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你真的想让他永远做你最亲密的朋友吗?没有更多点?”
“多什么?”
“他想娶你。”
“不,父亲,那是你和他父母想要的。不要把你的愿望强加给歇洛克。”
“我从没那样做。”他的眼光穿过我投向窗外。“我相信迈克罗夫特单独把马车驾回家了,所以歇洛克必须步行。我建议你可以驾车带他一段,如果你想要自己证实我的话。”
我看着我父亲几秒,然后快速离开。
我父亲是对的,因为我正好能够看见歇洛克的背影,月光把他影子投射在山上通往他家的路上,他看上去,很孤独。
我着急的走着,但是他腿比我长,步子比我大。他果然表现出一个不开心的男人的样子——如果我见过,我会那样形容的。
虽然父亲总是告诉我一个淑女是不应该用跑的,不过,我必须这么做,否则我永远也追不上他。我拎起裙子的下摆,握在手里,然后像头公牛那样不顾一切地跑了起来。在我们之间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我的追赶,但是他仍然埋头赶路直到我叫住他。
“歇洛克?”
我叫道。
他的步伐加快了。
“歇洛克,等等!”
我的声音里已带了命令的成分,那使他突然停了下来。我冲到他跟前,看见他用右手擦着眼睛。歇洛克·福尔摩斯已经17岁了,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说,他仍然可以哭泣,但是作为一个男子,他已经为此而感到羞愧了。
“你要干什么?继续嘲笑我吗?”
“当然不!”
“那么你来做什么?”
“我想和你谈谈。”
“关于报纸的分类?或者烟灰?或者尸体残骸?或者自行车轮胎的痕迹?”
“不,是关于什么在困扰着你。”
“现在,你就在困扰我。”
我张大了嘴吃惊地看着他。歇洛克从来没有用这样怨愤的语气和我说话。这好像一个耳光打在我脸上,我感到心被重重地击中了。
“那不公平。”我终于发现自己在回答他。
现在他也伤到我了。他让问题浮出了水面。
“我试着跟着你的建议,我真的试了,”他说,“但是迈克罗夫特比我做的更快更好,这让我沮丧。我可以任何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嘲笑我,但是两个——不。”
“我们不是在嘲笑你,歇洛克。我们在纠正你。”
我的话看上去只是使问题更糟糕了,所以我赶紧加了一句,“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这是克服它们的第一步。”
他的表情柔和下来了。我试着不用我父亲的理论去窥探他,仅仅用一种对待自己关心的朋友的态度去对待他。但是,我仍然仔细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于是我很高兴地发现父亲的说法是正确的。“一个只懂得数学的人怎么在这种私人领域这么有观察力呢?”我问我自己。歇洛克爱上我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但那是事实,那感情清楚地写在他脸上,清楚地就像是《泰晤士报》上的头版头条。
“回屋子来,”我说,挽起他的胳臂,“或至少去马厩。我来驾车送你回家。”
“你要驾车送我回家?”他问,有些不相信。
“是,我要驾车送你回家。我还要警告你哥哥,不许他以后不带你回家。”
“那太好了!”他叫起来。我们便走向马厩。
“就是这个笑容。我想你一定不小心把它放错地方了,现在我很高兴它回来了。”
“我也很高兴迈克罗夫特没有等我。”他满足的叹口气,“我更高兴和你一起回家而不是和他。”
他轻轻握住我的手,环在他臂中,我必须承认,一阵颤抖震动了我的身子。他那修长的手的轻微碰触深深触动了我。我抬头看他的脸,却无法在夜色中辨别那上面的表情,因为月亮已经在我们的背后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就是一个笑容,一个慢慢绽开的满意的笑容,一个我能在自己的脸上找到的笑容。
“你父亲在看着我们。”当我们经过图书馆时,歇洛克开口。
“我看见他了,”我回答,“但我并不担心,是他叫我出来追你的。”
“他鼓励你在这样寒冷的夜晚出门追一个发脾气的男孩?”
“只有那些他想我嫁的男孩们。”
“男孩们?复数?我有多少对手?”他胡乱抚着下巴,用那掩饰着他紧张的笑。
“那么,教授在玩凑对子的游戏?”他居然很快恢复了冷静。
“是的,不过你父母也在这么做。我真希望他们能在我们足够大的时候再来研究这个问题。事实上,我只有十四岁!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去讨论。”
“我正要去牛津就学。”
“恩,我知道——你一定在离开前把一生的规划都做好了?很好,那么,我们结婚后住在哪里?”
“伦敦,当然。下一个问题?”
“我们结婚后准备要几个小孩?”
“一个或两个。如果你要女儿就两个。第一个显然会是一个男孩。”
“显然。那么什么时候结婚?”
“我想最好等到你从牛津毕业。那么……从现在起八年之后?”
“好。除了做一个侦探,现在我没有任何计划。”
“嫁我不是那么一个糟糕的计划吧,不是吗?”
“我能想到更糟糕的命运。”
他好像不认为这是个笑话,他变得又一次认真起来,而我开始抚摩马的鬓毛来掩饰我的羞涩。
“艾米莉,我很抱歉。”
“为什么?”
“为我今晚的举止。”
“我已经忘了。不过,为什么你会那么生气?仅仅为了不知道两张报纸的区别而生气?那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极端的冒犯。”
“你说你已经忘了。”
“那么,我说错了。‘原谅’才是我要说的词。”
“我对你的举止实在是粗暴。”
“我理解你的不快。”他摇了摇头。
“我真的理解。”我加道,将手放在他的肩上。
他突然伸开他削瘦的手臂把我紧紧拥进他怀里,他的怀抱是那样紧密,几乎使我窒息。我像孩子一样,把头轻轻放在他的胸前。我不知道我们在这凛冽的寒风中站了多久,但是我们互相拥抱,不曾放开。
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时刻。
我们站在那里,像两个离家的孩子,因为一种无法言述却又相契无暇的情感而聚合在一起,因为理解,彼此拥抱,互相取暖。
即使在后来的岁月中,我和歇洛克总是试着告诉自己那一刻我们所感受到的并非爱情,而只是一种深切的友谊。然而,那个夜晚——在寒冷的马厩旁——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受了对方的存在。那是一个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场合,甚至比我们后来所经历的结婚典礼更加强烈地烙印在我们心头。无论我们的生命中还将发生什么,我们都坚信——我们拥有彼此。
通往Sherri ford Grange的路漫长而寒冷,但是对我来说,他仍然太短。一路上,歇洛克一直握着我的手。风呼啸着掠过,带来直达心头的冷,但感觉到手被歇洛克握住,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氤氲着我的胸口,使我无所畏惧。
是不是那就是爱情的感觉?
我想着。
或许那时我还不知道,甚至多年以后还无法了解。
但那是,那就是爱情的感觉。
我被这个微小却神秘的难题困住了,那是生活扔到我面前的新的难题:爱。
路上我和歇洛克几乎只字未谈。在我们的交往中,这是罕见的,因为我们常常毫无节制地相互嘲笑交谈。
但是这次,我们不需要言语。
那种感觉一直延续了下去,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我和歇洛克开始拥有无言的默契,许多重要的交流,我们不再依赖言语。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歇洛克会亲口告诉我他对我的爱,但是那并不重要。这一生,我都知道——他将永远属于我。
就像歇洛克和迈克罗夫特迷恋我父亲那样,我深深迷恋着他们的母亲。他们花很长时间在我身边学习侦探技巧,而我则花同样多的时间在维奥蕾特·福尔摩斯身边学习家务和女红。
不过很不幸,我不是一个好学生。
“翻动和搅拌的区别在哪里?”
我问。
“你加在勺子上的力量。”维奥蕾特耐心地回答。
维奥蕾特·丽本伦斯·福尔摩斯是家务之王,而我在这方面却是个小丑。她做家务从来不失手,而我总是干的很糟。看着我锅子底上惨不忍睹的东西,再看看自己锅子上成型的土豆泥,维奥蕾特善意地提出,“也许我们该从简单些的开始。”
不过,再简单的东西看上去我也做不好。我做的肉汁里总是充满了粗糙的颗粒;我做的炖菜总是湿搭搭。我总是烤焦了面包,把肉烧得半生不熟……而当我把一只外表漂亮的苹果派送来桌作为晚饭时,维奥蕾特骄傲地宣称,这是她的学生——我——的杰作。但是,我仍然犯了错——把盐当成了糖。那些晚餐的客人显然没有能礼貌地掩饰他们的……愤怒。
最后我想,或许只有一种事物我能不出任何差错地做好——三明治。
前提是有人烤好了面包、烧好了肉。
然后我们开始钩针编织。我的针脚却不是太紧就是太松,从来没有想维奥蕾特那样恰到好处。然后我尝试着缝纫。尽管我一直在努力,但是显然,我一直在失败。我浪费了数以公里计的面料,但是我始终不放弃。有一次我甚至想缝一条裙子!天,我到现在也不能想象我是怎么有这个念头的。我缝,然后拆开,我再缝,然后再拆开——周而复始,直到面料破损,无法承受我的折磨。
我听到了大厅里的脚步声,我相信那是我的一个学生来上课了。我也分辨地出他和他的哥哥的脚步声,所以我知道是哪一个来了。
“你好,歇洛克。”在他还没有来到图书室的门口时,我就向他打招呼。
“你好。你今天一直在缝纫吗?”
“我一直在尝试缝纫。”我说道,把那些玩意挪地离我远远的。“我想我实在不怎么精通。你在考虑一件很重要的事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承认你很了解我,但我想你还没有掌握读心术吧!”
“完全没有。我进行了观察,然后和我所知道的你进行联系。然后得出你正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费心的结论——完全依靠洞察力。”
“那么到底是什么,拜托,到底是什么引导你得出这样的结论?”
“有几条线索,不过最重要的是:胡萝卜。”
他向我弯腰,鞠躬。
“当然,也许‘观察’并非最恰当的词语,我闻到了你身上的胡萝卜味。所以我知道你碰过胡萝卜。”
“那没错。”
“你自己从来不会,当然,碰胡萝卜,所以,你一定是拿胡萝卜去喂什么东西了。”
他点头,“继续。”
“你身上还有另外一种味道:马的味道。当然,就是你喂食胡萝卜的对象。这些味道都很新鲜,所以显然最近你骑过马了。”
“我知道了。”
“正常的话你在早晨或下午的早些时候骑马,可是现在已经是下午6点了,所以你推迟了你下午的骑马时间。而你通常只在某些问题困扰你的时候才在额外的时间骑马。所以我推测,当你骑马的时候,你在考虑一个重要问题。”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骑马来这里上学的?”
“因为我看见你的马车停在外面。”
“我可以在套马车前喂马。”
“马车上的是灰马,只喜欢苹果和花生,而你经常骑的是匹爱吃胡萝卜的马。我还知道,你习惯用马儿各自最喜欢的食物来喂养他们,你非常善待他们。不过现在有一件事证明了我还是不会读心术——迈克罗夫特怎么没有和你一起来?”
“迈克罗夫特最近过着久坐不动的日子,他想要的全部就是坐在椅子里阅读关于政治的书籍。”
“政治?”我问,“那该多么令人厌倦!”
“他已经决定要为政府工作,不过我永远不明白那是为什么。父亲对他非常失望,所以现在看上去遗产要归我继承了。”
“你父亲改了遗嘱?”
“就我所知,没有。但是他最近频繁地与律师会面。”
我嗤嗤地笑了。
“什么那么好笑?”
“我不能想象你一副乡绅的模样,歇洛克。”
他展开一个笑容,然后加了一句,“我也不能。”
然后他的笑容消失了,就像他出现的那么快。
“怎么了?”我问,推了推他的肩膀。
“我一直想问你一些事。”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他要向我求婚吗?在过去四年中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但是现在?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清了清嗓子,我脑海中奔腾的思绪便突然都宁静下来,所以我能全神贯注的倾听。
“我在想……你是否介意我和一起去伦敦,做侦探?”
我有些失望,但却同时松了一口气。
“为什么我要介意呢?”我问,“你会是一个最棒的助手。事实上,我能够预见到很多机会的门拒绝向女性打开,但是如果你和我一起工作——我相信我会做到更多,做得更好。”
“那就好。我多么希望你能答应!”
“我怎么能拒绝这么一个请求呢?离开我亲爱的歇洛克,我还能做什么呢?”
他还我一个微笑,然后他的凝视开始变得灼热起来,他紧紧地,看着我的眼睛。
他想要吻我。
但是我也从他漂亮的灰眼睛中看到畏惧。
我和歇洛克彼此了解已经有9年了,但是现在我正在成为一个女人。他绅士的天性使他对于产生吻我的念头而感到吃惊。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吻,我想在把他从那奇怪的状态中拉回来之前,逗逗他那烦乱的心情。我知道,那有点残忍,不过观察他充沛的情感所导致的难为情使我获得了一种乐趣。情感是歇洛克平时比较缺少的东西,所以一旦他被感情触动,变得有些紧张,那真是很好玩。我伸手触了触他的脸颊,他却阖上了眼,逃离了我的视线。我没有挪开我的手。
“歇洛克,请——”我说,“我请你,不要转开。”
他只是摇了摇头。
“我们之间总是坦诚相对,我不希望想改变目前的事实。”
“我不能面对你。”他说,“我害怕。”
“为什么?”我问,但同时意识到他的回答将是怎样的。
“我的念头使我羞愧。”他的声音在颤抖。
“歇洛克,看着我,”他再次摇了摇头,双眼仍然紧闭。我伸出手,引领着他的头转向我。他慢慢地张开眼睛。
“歇洛克,我要你……吻我。”
他的眼睛一下子张开了,当闭上时,他吻了我。
他真的吻了我,轻柔的,随后变得坚定而热切。
我感到膝盖不听使唤,我想如果不是他那么有力地将我拥在他怀里,我一定会晕过去的……
当一个人从逻辑学的角度去观察,一个吻仅仅是一个机械的动作,平淡,甚至令人厌恶。
我就是常常这样想的,所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的初吻将是平淡无奇的。而现在——如果那个人不是歇洛克,我想我的结论应该是对的。然而我低估我对这位出众的男子的情感。天,我以前是如何能把他当成我的朋友?
我完全没有准备好如何去回应他,恐怕,他因为没有准备好来回应我。
“恩哼。”我父亲清了清喉咙。
“父亲!”我喘着气。
“教授!”歇洛克叫。
“孩子们,不要让我打扰你们的热情。我是来找一点工作的资料的。”父亲从我们身边走过。
“父亲,如果你要找你关于小行星动力学的资料,他们就在那个桌子上,早餐前你把他们放在那里了。”
“哦,是的,我忘了……”我父亲说。
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忘记。
在我父亲的生命中,他从来没有一次忘记过他的笔记。当我发现他根本没有去注意桌上的笔记时我确定我的怀疑是正确的——他绝对没有忘记笔记在哪里。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希望这个尴尬的时刻能够延长,也不确定他在那里观察我们已经多久了。平生第一次,我的观察能力不见了,而那仅仅是因为一个吻!
就像以往那样充满了绅士风度,歇洛克过来替我解围了,虽然我不知道,他眼中的勇气是哪里来的——要知道,几分钟前,里面还满是畏惧。我想那一定是他的深情给他的回报吧。
“教授,您能给我这个荣幸让我娶您的女儿吗?”
我父亲笑了,终于挪到书桌前。
“我一直在想你要多久才肯这么说,我的孩子。从我们之前的谈论,你一定知道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了,但是我建议你问我的女儿。”
歇洛克转向我,然后单膝跪下,轻轻执起我的手,“我亲爱的艾米莉,可以吗?”
“你知道我会答应的。”我听见我轻声的回答,“但你应该先问我!”
“你们两个一定有很多东西要商量,”父亲边说边往门走去,“所以我应该离开了。”
教授走后,歇洛克终于站起来,“我怎么能向你求婚呢?我甚至不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吻你!”
“有的时候,你的害羞相当迷人。”我说。
“有的时候,你的自信让你的威胁相当迷人。”他回答。
“我从来没有威胁过你。”我辩解道。
“没有,但你常常成功。不过……迈克罗夫特这几天可能要对我有意见了。”
“为什么?”
“他也准备向你求婚。不过总算有一次弟弟赢了。”
“迈克罗夫特?天啊!”
“你的观察能力失算了吗,艾米利?”
“我想是的。当观察能力遇见找丈夫的难题时,歇洛克,在那个世界里,我只看得到你。”
“我和艾米利订婚了。”
在那天的晚餐时分,歇洛克宣布了这个消息。
福尔摩斯太太显得很高兴,但是他父亲却反映平淡。尽管在这之前他就应该料想到这样的一个场合,他从来不赞同他儿子的做法。任何他儿子做的事,他都要找点茬。
“你们太年轻了。”他简短地回答。
“我不明白,”歇洛克说,“你总是说希望我们两个结婚。”
“你们就是太年轻了。”
“我们又不是明天就进教堂,父亲。”
“歇洛克,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
歇洛克永远不能忍受别人对他智力的侮辱,而他父亲的举动的确激怒了他。
“但是,我从来没有像您一样围着年轻的女仆转悠,如果那就是你所指的‘了解’的话。”
他父亲顿时青筋爆起,愤怒而难堪地红了脸,接着像暴风雨一样冲出了饭厅。
“威廉·歇洛克·福尔摩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福尔摩斯太太问道。
“我很抱歉,妈妈。我并不希望您在这样的情况下听到这些。”
“听到?歇洛克,我早就知道了。”
“怎么——”
“你认为你是从那老上校那里得到你的观察和推理能力?那个老头?拜托!”
“如果您知道,您怎么能忍受呢?”他问。
“男人堕落,女人接受。那就是时下的世界。”
“我不会接受。”我声明。
“而我不会堕落。”他接道。
“那么我祝福你们都能在婚姻中得到幸福。不过你们的确太年轻,也太理想化了。”
“理想正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妈妈。当我们许下承诺时,我们就拥有了彼此。”
“那我希望你们永远保留这份理想,我的孩子,我真的这么希望!”
歇洛克告诉华生医生《格洛里亚斯可特帆船案》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个案件。那是对的,因为小特雷佛的确向他求助了。但是虽然《格洛里亚斯可特帆船案》是公众所知道的他的第一个案件,而事实上,那是第二个。我和他共同参与了第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离我家很近。事实上我们并不上被雇佣而去调查案件,而是瞒着我们的主顾来进行。
这个主顾,就是我父亲,杰姆斯·莫里亚帝教授。
对于我们所作所为,我们现在仍然感到痛心。
那时我父亲在Exter 任教时,四周有很多关于他的谣言。这些谣言传播的是如此厉害以至于我父亲几乎不得不辞职。当他把这告诉我时,我很生气。、
“我们要为您洗清名誉,父亲。”我说。
“那不着急。艾米利。”他回答。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的尊严呢?您的职业呢?这是当务之急!”
“不,我亲爱的,这事不重要。”
“不,父亲。”
“我已经辞职了。而福尔摩斯上校已经利用他的影响力已经为我在伦敦找了一个军队教官的职务了。”
“我必须把洗清您的名誉作为我的任务,父亲!”
“你不需要自找麻烦,我的孩子。”
“自找麻烦?!父亲,您在说什么!如果您认为这个问题超出了我能力的范围,那么,我相信,歇洛克会帮助我。”
“不,艾米利,我知道你一个人就能完美地解决这事,但是,我不允许。”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我禁止你这么做。”
“您从来没有‘禁止’我做什么事,父亲。”
“也许以前我太宠你了,现在我要开始严格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这样。我已经听够你玩弄的那些愚蠢的侦探游戏了,我真的听够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觉得自己是如此地无用。当那天歇洛克到我家时,他看到我在哭。
“艾米利?”他在我身边坐下,轻轻地环住我的肩膀。我将自己藏进他的胸怀,像孩子一样抽噎着。
“我亲爱的,请告诉我到底怎么了。”我尽量止住泪水,试着开口说话。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我只好断断续续地把单词连起来,说给他听。
“由于流言,我倒霉的父亲被迫辞去他的职务,而他竟然不允许我去做些什么来证明他的清白!那深深伤害了我,歇洛克,我觉得我太没用了!他不让我帮他……”
“究竟为什么?”
“他说那是因为他已经受够了我那些‘愚蠢的侦探游戏’了,他完全禁止我参与到他的事务中来为他正名。”
“那么,你不会让那些停住你的脚步,对吗?”
“当然不。你会帮我,是不是?”
“我永远在你这边。”
“谢谢,歇洛克,你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当你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这个未婚夫如何能不站在你这边呢?”他更紧地拥抱了已经哭了好久的我,“我可怜的艾米利。“他抚摩着我的头发。
“我把你的外套毁了。”我说。
“我会另外买一件。”
“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调查?”
“我肯定,我们需要和大学里的一些人进行交谈。对你来说,调查你的父亲会有点不方便。”
“那么你是要把我赶出调查罗?”
“当然不。我只是在建议你用一个化名。”
“哦,我向你道歉。今天我太急躁了。”
“完全理解。”
“那么……艾米利·切尔尼(Emily Chrane)怎么样?你认为那能过关吗?”
“这个名字很好。”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早上。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睡一觉,这样我们才有充沛的精力进行我们的调查。”
“今天晚上我一点也睡不着。只要我脑子里有一个疑惑,我就睡不着。”
“我也不行。”
他想了一会,“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一个淘气的笑容在他脸上浮现。
“歇洛克。”我轻声地说。
“恩?”
“我不喜欢你的眼神……”
“什么眼神?”他无辜地反问,然后开始轻轻地吻我的颈,“你应该要开始学会习惯……”他在我颈项间低语呢喃,“……习惯这个眼神……如果你嫁给我……你要习惯他……因为你会经常看到……”
“歇洛克,噢……歇洛克……”我叫着,却无法抗拒,“我们得想一下明天的调查的。”
但那没有能够延缓他的动作,“歇洛克……请……停下,好吗……”我试着将他推开,但他将我拥得更紧。
“如果你吻我一下,我就停住。”
“好吧。”我叹道,快速地亲了他一下。
“噢,我肯定你可以做得比那更好!”
“你没有叫我认真地吻你。”
“来吧,专心点。”
“我想只要把嘴唇用上就可以了。”
“哦,没有关系!”他不耐烦地手,松开了手,坐回沙发里去。
我给他一个热切的眼神,掂手掂脚地凑到他跟前,尽我所能地吻了他。
“这还差不多,我知道你用心了。”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工作了吗?”
我从父亲的书桌上拣起一个信封,打开并阅读了里面的信件。
然后,我浑身冰冷。
歇洛克正在浏览一堆文件,所以他没有看见我突然之间的僵硬。
“艾米利?”他终于发现了我。
我却过于惊愕而无法回答他。
“艾米利,那是什么?”他走到我身后。
“这是真的!”我说,把纸片从我眼前扔开,“那些谣言是真的!”
“这不可能!”他拣起纸片看着,随即像崩溃一样跌到在沙发上。
“不,”他轻叫,“我不相信!教授不可能是罪犯!”
“他是,歇洛克,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他是!我们都被我们对他感情所蒙蔽了!”
“我们得在他发现我们之前离开这儿!”
我们开始整理文件,把他们放在原来的地方。
“一切都归于原位了。”他说。
歇洛克为我开了门,接着,当我走进大厅时,我和父亲撞了个满怀。
我低低地叫了一声。
“我告诉你不要管,艾米利。”他说。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我回答。
这一刻,我的愤怒取代了我对他的敬畏。
“那么你要我选哪个?一点小小的谣言与耻辱?还是被你唯一的孩子发现你是一个罪犯?”
“迟早我都会发现事实的。”
“我认为我也许能隐瞒你足够长的时间,当你嫁给歇洛克,离开我以后,我就不用担心被你发现了。如果我能说服你不要插手这事,这愿望就能实现。但是,倔强如你,一定会想要知道全部的事实。现在,你知道了一切,我希望你能够满足了。”
“恰恰相反。”
“你准备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
“什么也不做?”他问,“那么你要做侦探的梦想呢?你对正义的追求呢?”
“这一次,我会忘记我所知道的。但我也希望,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活了,再也不要了。”
我缓缓地拖着身子离开大厅,歇洛克跟着我。
“你去哪儿?”他问。
“任何地方。我不在乎了。只要离开这里就好。”
我加快了步伐。
“但教授——”
“再也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名字。”
“你不是认真的吧?”
“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
我发出一声刺耳的叹息。
“但是他是你父亲!”
“再不是了。”
“你爱他!”
“我再也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甚至当他和我联系在一起?”
“爱是如今的我们都无法承受的伤痛。”
“艾米利!”
“歇洛克,你完全无法想象我现在心里的痛!”
“你太自私了!”
他大叫,“你知道吗?这话伤到我了!”
“他不是你父亲。”
“的确不是。但是他是我的岳父。与我父亲相比,我对他怀着更深的尊敬和热爱。”
歇洛克和我在一起时,总是文雅而温和。甚至当极少数情况下我的情绪波动超出了我所能控制的范围时,他毫无疑问是我最坚实温和的避风港。
现在,他用力抓住了我的臂膀,把我的脸转到他的面前。
“噢,歇洛克!”
我一下子崩溃在他的怀里,泪水刹时奔涌而出。这是我成人以来第二次哭泣,而歇洛克却充当所有两次的见证人和安慰者。
“那么,你现在打算做什么?”他问。
我不愿正视父亲是个罪犯的现实,“我准备离开这儿,到牛津去念书。”
“我不知道,总会有办法的。我自己存了点钱。”
“我会给你我的学费。”
“不,歇洛克,你不能!”
“我能,而且我会。”
“但你的父亲-——”
“我不在乎我父亲说什么。”
“我不会允许你那么做的。”
“听着,艾米利,就算你是我的私人推理老师,我也不得不说,在这个社会,除非你有文凭,否则一个女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只有你拥有了文凭,人们才会认真地对待你。你必须拿到一个学位,如果可能的话,多拿几个。而我却不需要这些。事实上,我为小特雷弗做的那事已经证明你把我教得足够好。让我们试试,能不能用这点儿才能来支持你上学的费用。”
“不,歇洛克,我不能。”
“你说过你回嫁给我,但是你为什么不让我帮帮你呢?或许我一点也不了解你。而现在我想我感受到当教授拒绝你的帮助时你心里的感受了。”
“歇洛克,那不值得。”
“或许。但你想过吗?你想要帮助教授是因为你爱他,而我想要帮助你是因为我爱你。”
“你不需要向我证明什么,歇洛克。”
“请不要这么说。就这一次,请你忘记你的独立与倔强,请让我来照顾你。”
“我恐怕只能这么做了。这一刻,我所有的选择权都没有了,就像这一刻我变成了孤儿一样。”
我们漫无意识地走着,直到来到歇洛克家。福尔摩斯夫人很高兴地把我们迎了进去,并把我安置在客房过夜。而我和歇洛克则只字未提这个下午我们所经受的灾难。
当未来重重地压过来,我们只能说,有些事总是难以解释。
歇洛克转动钥匙打开门。这间位于蒙太格街的小公寓,将要成为我们的新家。房间昏暗而狭小,灰尘遍布的地毯和暗淡的隔墙充斥着整个房间。虽然歇洛克在这里只居住了两个月,可房间里已经弥漫着化学试剂浓重而呛鼻的味道。
“我知道这儿不怎么样,但是直到业务好转前,这是我能承担的全部。”
“这儿完美极了。”
“你在开玩笑。”他说。
“我没有。这儿很舒适,也没有花俏的装饰,要知道家务可不是我的强项!所以,这里很好。”
“你总是看到事物最积极的一面,即使要住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
“我们不是住的简陋,”我回答,“是住得简单。”
“只要你喜欢,随便怎么叫吧。等我一会儿。”
他把我的行李拿进去,然后转过身来,将我抱起,拥在他的怀里,带我跨过门槛。
“歇洛克,放我下来!这个传统愚蠢透了!”
“不,你不想错误地踏出我们婚姻生活的第一步吧?”
他用膝盖轻轻关上门。
“当然不,但——”
“纵容我这一次吧。我们可不是每天都结婚!”
他终于把我放在了房间正中的小地毯上,然后转身将门锁上。
“你最好不要再做第二次了。我亲爱的丈夫。”我说。
当他穿过房间向我走来,当我将手穿过他的乌发,随着一声轻微的叹息,我被他拥进了他的臂膀。
“我喜欢这样的称呼,我亲爱的妻子。”
然后他缓缓而深情地吻住了我。
从此我们开始了我们的婚姻生活。
--------------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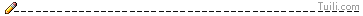
|
我始终在渴望,
在深秋的伦敦街道,
与你擦肩。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主题版区 > 福尔摩斯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主题版区 > 福尔摩斯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