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qiking(小丸子) qiqiking(小丸子)
|
|
|
1 楼:
论福氏之在中国之引进
|
04年03月12日23点23分 |
论福氏之在中国之引进
早在19世纪末,福尔摩斯就来到了中国。最早的探案译述可以追溯到1896年9月《时务报》第6册开始刊载的张坤德编译的4篇《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即《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记枢者复仇事》、《继父班女破案》、《呵尔唔斯缉案被 》。继起的有1899年素隐书屋刊刻的丁扬社译的《新译包探案》,1902年《续译华生包探案》, 1903年《补译华生包探案》, 1904年奚若、黄人合译的《大复仇》、《案中案》、《恩仇血》等。1904年至1906年,小说林社推出由奚若译《福尔摩斯再生案》多卷本.1906年堪称是福尔摩斯翻译的大年,先后出版的有鸳水不因人译《深浅印》(小说林社);林纤、魏易合译《蛇女士传》(商务)、马汝贤译《黄金宵》(小说材社)以及佚名译《福尔摩斯侦探案第一案》(即《血字的研究》),1908年林纾、魏易又将此案译为《歇洛克奇案开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翻译之部》统计,福尔摩斯探案仅单行本就多达25种。
据阿英《晚清小说史》:“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上”,“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的”。近代中国人理解西方文学首先是从小说开始的,而在西方小说中,接受最早、理解最快的是侦探小说。在侦探小说译述方面,又以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为大宗。当时的文人可以说很少是不读福尔摩斯探案的。1903年孙宝瑄在日记中称福尔摩斯探案《鹅腹蓝宝石案》内人物“吞吐风雅,用字犹谨,足证为饱学之士”,认为“其情节往往离奇俶诡,使人无思索处,而包探家穷究之能力有出意外者,然一说破,并合情理之常。”周桂笙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中,称赞福尔摩斯其人“机警活泼”,所破各案“往往令人惊骇错愕,目眩心悸”。林纤认为《歇洛克奇案开场》“文先言杀人者之败露,下卷始叙其由,今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而书中故为停顿蓄积,待结穴处,始一一点清其发觉之故,令读者恍然”,这就如同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讲的“传神阿堵”。认为侦探小说实是一种“足发人神智”的“理想之学”.陈熙绩甚至认为林译可以当作《史记》那样来细细咀嚼。“福尔摩斯”可以说是与“茶花女”齐名,成为晚清文坛最走红的外国小说人物,这一译名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智慧人物的代名词。
到了民国初年,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中译本继续在递增,所有探案的翻译已初具规模,编印全集已成为可能,并为读书界所渴望.1916年刘半农与“髻龄即喜读”福尔摩斯探案的程小青、严独鹤、天虚我生、陈霆锐等一起,译出了探案全集12册,由刘半农负责全书的校编。他将“前后四十四案细读一过”,并撰成《英国勋士柯南道尔先生小传》一文。他在全集跋中对44案作了一个鸟瞰式的分析。认为“全书四十四案中,结构最佳者,首推《罪蔽》一案,情节最奇者,首推《獒祟》一案;思想最高者,首推《红发会》、《佣书受给》、《蓝宝石》、《剖腹藏珠》四案;其余《血书》、《杀父案》、《翡翠冠》、《希腊舌人》、《海军密约》、《壁上奇书》、《情天决死》、《窃图案》诸案,亦不失为侦探小说中之杰作。惟《怪新郎》一案,似属太嫌牵强,以比较而言之,不得不视为诸案中之下乘。而《丐者许彭》一案,虽属游戏笔墨,不近情理,实有无限感慨,无限牢骚蓄乎其中”。刘半农认为,“以文学言,此书亦不失为二十世纪纪事文中唯一之杰构。凡大部纪事之文,其难处有二:一曰难在其同;一曰难在其不同。全书四十四案,撰述时期,前后亘二十年,而书中重要人物之言语态度,前后如出一辙,绝无丝毫牵强,绝无丝毫混杂”。其中福尔摩斯、华生与莱斯屈莱特等“数人栩栩欲活,呼之欲出”。各阶层人物的“言语举动一一适合其分际,而无重复之病,亦属不易”。从文章总体布局上看,“《蓝宝石》与《剖腹藏珠》,情节相若也,而结构不同。《红发会》与《佣书受给》,情节亦相若也,而结构又不同。此外如《佛国宝》之类,于破案后,追溯十数年以前之事凡三数见,而情景各自不同。又如《红圈会》之类,与秘密会党有关系之案,前后十数见,而情景亦各自不同。此种穿播变化之本领,实非他人所能及”。此书书前还有当时文坛著名作家包天笑、陈冷血等的序。该探案全集1916年5月初版后销路看好,3个月后就再版,20年中出了20版之多。_
中华书局1916年版的这部《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的畅销,使其他一些书局大为眼红,1917年商务印书馆即出版了刘延陵、巢干卿译的《围炉琐谈》;世界书局的主持人沈知方提出要已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塑造了中国福尔摩斯一霍桑形象的程小青,把中华版以后柯南道尔续写的福尔摩斯探案一起收罗在内,另外出一部《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并把它们译成白话文,加用新式标点和插图。1927年该全集由世界书局出版,共收柯南道尔的侦探案54篇。1934年又改头换面出了程小青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上、中、下三册。1936年上海春明书店有胡玉书译《福尔摩斯新探案》上下册;1937年上海武林书店和侦探小说社同时推出徐逸如译、何可人选辑的《福尔摩斯新探案大集成》12册;1937年6月上海大通图书社出版有杨逸声编译的《福尔摩斯侦探大全集》8册。
尽管福尔摩斯探案在近代中国一直是最畅销的外国小说之一,但文坛学界似乎对之并不怎么看重,甚至还颇有微词,如郑振铎就认为,林琴南译出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属于二三流的毫无价值的书,是虚耗宝贵的劳力。鲁迅1932年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也认为,那些包探案,“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事实上,侦探小说的作用实不应低估。在清末中国小说翻译史上,侦探小说是最早离开日本翻译这一中介,直接从欧美译述的少数几个小说品种之一,据日本学者中村忠行《清末侦探小说史稿》研究,似乎在步伐上甚至比日本还要快。侦探小说作为文学中重要的一支,在“情”与“智”方面占优势,在接受过程中给读者以强烈的参与意识,使读者与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起去观察、探究、集证、演绎、归纳和判断,这种阅读行为是其他文学题材难以产生的。在结构的奇巧,布局的致密,脉线的关合和对话的紧凑上往往较其他小说为胜。正如刘半农在《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中所言:“以比较的言之,侦探之事业,应变在于俄顷之间,较之作小说者静坐以思,其难不啻百倍。”程小青专门撰文论述侦探小说,在《谈侦探小说》一文中认为,在写“惊骇的境界,怀疑的情势,和恐怖愤怒等的心理,却也是以左右读者的情绪,使读的人忽而喘息,忽而骇呼,忽而怒瞪欲裂,忽而鼓掌称快,甚且能使读者的精神,会整个儿跳进书本里去”。无怪乎福尔摩斯探案如此受中国读者的青睐,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在《日本推理小说与清朝考据之学》一文中,回忆自己在私塾中很爱读侦探小说,“从文言的柯南道尔著《福尔摩斯侦探案》,到白话的程小青著霍桑、亚森罗萍侦探案,以至《侦探世界》杂志等,都在极力搜求之列”。
除此之外,侦探小说往往还含有“智”的意味,可以扩展人们的理智,培养人们的观察力和增进人们的社会经验。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说,侦探小说也带来了西方社会的一些法制观念和人权思想,这对于习惯读《施公案》、《彭公案》、《龙图公案》的中国读者来说,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远比人们估计的要高。侦探小说的输入,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变异中也具有积极的价值。陈平原所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指出,《福尔摩斯侦探案》一译过来就有人模仿,尽管它算不上文学名著,可却切实地帮助“新小说家”掌握了倒装叙述手法。《老残游记》就借白公之口,称老残为“福尔摩斯”。被誉为“中国侦探说部之鼻祖”、“中国侦探小说之第一人”的程小青,正是借鉴了《福尔摩斯侦探案》的写作手法,创作了数十部80余篇《霍桑探案》。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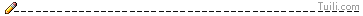
|
|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主题版区 > 福尔摩斯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主题版区 > 福尔摩斯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6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