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venth(七七) seventh(七七)
|
|
|
1 楼:
[春季活动8]莺娘(聊斋)
|
03年02月10日11点03分 |
*****
先打个预防针,写完发觉,这个,推理的味道实在是淡了一点,到后来变成恶俗爱情主题了,汗,想不发了,但是觉得写得好辛苦,所以决定还是不管三八二十八牵出来遛遛。硬着头皮安慰自己:反正是另类推理,重音放在另类上,打个擦擦擦边球好了。又想在括号里写上(聊斋+爱情),又觉得聊斋本来就有很多是爱情的,这样属于多此一举,说不定还会降低点击率,于是又算了。又想是不是该写上(白话聊斋),又觉得愈发废话,我还能写出文言文的东西来?
总之是想想想想想……最后总算心一横,眼一闭,我帖!就这样贴出来了!汗……我怎么想了这么多!!!!
呵呵,所以,总之,大家不要笑我啊。先谢过了!
*****
我不甘心。
枉死城内无日月,我独独地重复着这句话。
都说,杭州知府程大人晚年纳得一房侍妾,虽不是什么名门闺秀,却是貌美能使西施妒,舞作轻虹飞燕惭。是以艳福不浅。
呔,不过是些街头巷尾无聊揣测罢了。舞作轻虹?到如今,还应了这句话了。原来魂灵当真是这样没有份量的东西。飘飘荡荡叫人好不难受。也罢,又有什么关系呢?老爷喟叹几句,夫人面上必定不悦,倒是庆儿那丫头或会落下几滴泪来,算有人为我哭过了。
西子湖畔那道朱门后,几时少过笙歌?谢氏莺娘讨过欢喜,又岂是少不得的?
可是,我不甘心。我狠狠唾道。
我甚而不知道是谁给我这一刀。
那日元宵,老爷夫人携了小姐们赏灯去。莺娘无事,闲做些女红。只听门吱呀一声,当是庆儿端了茶点来,不曾回头,却只觉背心倏忽一凉,接着便是腔子里撕绞的痛,那刀上下了毒,来不及娇呼一声,回头已是这枉死城里女鬼一只。
这叫我怎生得甘心?
进府两年,夫人颐指气使横竖挑剔,我都忍下。从未想过要什么地位身份,再者说,夫人黄氏娘家殷实,又生养了二女一子,岂是区区的我可以动摇的?
爹久读圣贤书却不得志,娘重病,几无以为炊。一日,莺娘浣洗衣裳,撞见知府大人的官轿,三日后,聘礼送到家中,爹狠心一点头,莺娘便进了程府。虽家贫,往日里也是读过诗书,识得礼数的女子啊,莺娘晓得做了侍妾得处处谨慎,不得造次,只道是命,却有人竟要连我这命都夺去!下手这样狠!
然空自不甘,何用之有?以为不再会有人顾得我这一缕怨气,忽一日却被提了出来。
兀那女鬼,你虽枉死,然今日杀你之人已伏法,一命偿一命,果报清算,你即可去转世投胎。阎罗殿上森森地传下话来。阎罗殿下血淋淋身首异处地倒着一滩。
杀我之人?我也不曾看见的,竟这样轻易地伏法?生时不曾有人问我寒暑,死后竟有人来替我申这积踵之冤?我蓦地诧异,不敢相信。
堂下吴福生魂,你且将所犯之罪道与谢氏莺娘。
吴福何人?我不曾听过。
下人吴福,在谢府伙房当差,早知道二夫人得老爷恩宠,当有些值钱的珠钗,想谋来换些银两,便……血肉模糊里传来背书一样没有声调的讴哑话音。
不等语毕,我这厢里已捺不住狂笑起来。生前死后不曾有过得放肆,悉数爆发出来。
什么果报清算?阎王老子你也有糊涂的时候么?这哪里是什么杀我之人,不过一只和我一样的枉死冤魂啊,好了好了,这本是不需想也明白的理儿,知府上偏房被杀了总该有个填坑的死鬼,官府文章,屈打成招。阎王老子你妄得虚名,竟连这把戏也看不穿么?
兀那女鬼,岂有此理。
阎王老爷,你抓错人了。
兀那女鬼,何错之有?
阎王老爷,你倒想想,企有鸡鸣狗盗的下人,在元宵之夜到主子房里谋珠钗?即便来了,他又是如何谋得的这舔毒的刀?阎王老爷,那一日我不曾回头,可倘我回头,他如何交待?不是他,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下人?那人有备而来,倘我回头,看到得必是一张笑意盈盈的漂亮面孔,那刀子必也出来得晚些。阎王老爷,我不甘心,这算什么,这样胡乱地把我搪塞了么?阎王老爷,我——不——甘——心!!
莺娘我活得一世,恐也不曾这样嚣张说话,是这积怨化作了唳气。说罢自己都骇然,虚妄里摸一下面颊,唯恐已是发青,而口中长出獠牙。那是那般厉鬼的模样。不,莺娘一直是本分克己的,莺娘不要做那骇人的厉鬼,莺娘只是心有不甘啊,想那个害我之人伏法啊……
那依你要如何?
依我?竟可以依我么?莺娘一世里都是听话的份,未进程府时候,尽了十七年做女儿的本分,进了程府,又规规矩矩伺候老爷两年。到了竟可以做回主张么?好,阎王老爷,那就请你再许我些时日,等莺娘找到这歹人,让他得了报应,即刻就去投胎,决不为非作歹。
兀那女鬼,你虽寿数未尽,但肉身已葬,又如何能还阳去?
阎王老爷,莺娘名唤里带个莺字。你就借莺娘一个莺鸟之躯吧……
莺莺燕燕西子湖,已是初夏时分。原来地府里的时日快过人间,那般浑浑噩噩,便是三月光阴。
我循着记忆,飞入那堵粉墙。别院空空置着。这般不吉的地方,出事以后,怕就不再会有人来碰了。窗纸上落了灰,啄破了,但见房里一切如旧。那些绣花的旧家什散散扔在那里,只不见了那日绣着的一方鸳鸯枕巾,总是弄脏了,扔掉了。老爷虽称莺娘好女红,但这不曾绣好又溅了血的东西,自然不会有人要。几案上黯黯一抹黑,我一惊。那是血啊,是莺娘的血,还不曾褪尽。
那一日,那一日,记忆好像是要冲破头脑出来,那一日,为什么是那一日呢?
莺娘,今日元宵,举家赏灯,你当同往。还记得那日清早请安时候,老爷话音未落,那边夫人轻咳一声。哎,莺娘岂是不知礼数之人。忙道昨夜受了风寒,身子不适,怕不能陪老爷。
还真是比千金小姐都娇贵,夫人接上话头,不养好身子,怎么侍奉老爷,传程家的香火?你且在别院里养着吧,叫庆儿熬些汤药,不要老是抱病。
话都叫她说去了。莺娘喏喏,还要靠我来传什么香火?都说大少爷双十韶年,玉树临风,又是尽人皆知的才子,仕途坦荡。哪日中了状元叫皇上挑了做女婿也未可知啊。罢了,这些都是无关莺娘的事情,莺娘且守好自己的别院就是了。
庆儿听话,当真叫伙房熬了药,夜里端端地捧来房里。这丫头是进府时候夫人赏的,程府上下,也只有她和我说说话。雪鸿碧霓两个小姐倒不若她们的娘那般嫌我。虽叫着二娘,其实不过小我三四岁,大户人家的小姐养在深闺,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是索然,偶尔会来别院向我讨个绣花样子,可是这二娘的名头隔着,总是交不了心的。
庆儿,你知我抱病是假,且平素里讨厌汤药得紧,还是端了回去吧。我道。
可是,这是太太吩咐的呢。小丫头面有难色。
倒了这汤,药炉子还去伙房好了。我低头刺绣,只听得庆儿出门去,些许,又有人推门进来,以后,以后就是那一刀了!
我好像还可以感到腔子里那阵痛。我不甘心,这人是谁?
停在梁上,我有些惶然,这人是谁?好难。一厢情愿要找那个歹人,原来不是容易的事。
当时我认得的人啊,若那一日我能回一下头,能回一下头也好,怎的就没有回头呢?会是谁?我细细排摸起来,总该是常来别院我不会起疑的人,老爷?两个小姐?夫人?那一晚上,他们是一起赏月去了的。再者说,为什么呢?就地是谁和莺娘冤仇这样深?要取我性命?便是夫人嫌我,也不至此啊?
想不出来,总不会是庆儿,更没有道理了。况且她也没有这份量,好叫那个吴福顶了罪。
对了,我不在了,庆儿哪里去了呢?得要寻一寻。
到了花园,在一支春桃上落下来。哎,貌美能使西施妒,舞作轻虹飞燕惭。怎的又想到这两句闲话,也不晓得是谁传出去的。都说得象什么名伶了,荒唐得紧,好笑,啼出声来,倒叫嬉戏着的二小姐见着了。
姐姐,姐姐来看,这里有只莺儿,端得好看。碧霓一阵娇笑,十四还是十五了?从来没心计的孩子脾气。不会,不会是她。
我歪头望着她,她便又笑,姐姐,你看着莺儿也不怯,倒好似看着我,性灵着呢。
性灵?我一惊,噗啦一下飞起来。明知道不会有人晓得这莺儿竟是过往的二夫人,却还是心虚得很。
隐隐听得厢房里大小姐的声音传出来,碧霓别闹了,爹娘心绪不好,听得你笑闹,又要恼了。
不对呀,老爷夫人为什么要恼?雪鸿碧霓,一直都是这家里的心肝宝贝,碧霓又向来是这样子,老爷见了,欢喜还来不及,怎的会恼?雪鸿说,他们心绪不好,心绪不好?为什么?出了变故么?
好似有些蹊跷,我重又落回枝上,细细听那姐妹两个的私房话。
也是呢,碧霓清叹一声,我们家这是中了蛊了么?先是二娘出了事,然后哥哥又一病不起,真不晓得怎么回事。
那么,是少爷了?少爷,忽然发现,这程家上下唯一的香火对我这个二娘,几乎是空白的。我见过他的,一次,两次?也许更多一些吧。或许他叫过我二娘,也只是场面上的文章,二娘?他还长我一岁呢。但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嫁到程家,不过是为了娘可以有那份聘礼看病吃药,家里面日子过得下去。少爷亦不会如两个小姐那般偶尔来我厢房,想想,除了那些众口一词的称许,我都不曾端详过他的面孔,貌比潘安,是这么说的?他如今病了?
当是元宵以后的事情了,否则我不会不晓得,会有什么关联么?我且听下去。
是啊,不晓得是遭了什么难,什么药都不灵,大夫说是心里有郁结解不开,失了神志。雪鸿淡淡道来。她长碧霓一岁,城府却深得多,心里藏的多过说出来的。
郁结?哥哥能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真是……碧霓嘟起嘴来。怎的不是,这府上的公子小姐,哪个不是蜜糖里泡大的,哪里会有不如意的事情?我暗下思忖,也是命啊,叫人眼红呢,不知世间疾苦的少爷,会心病郁结?那么,如莺娘一般,还真应该谢谢那个赏我一刀了结我的人呢,好转世投个好人家。
发愣之间,又叫碧霓看见了。
姐姐你看,又是这莺儿呢。往日里从不曾见过的,可是把巢筑在这花园里了?姐姐,我们要是拘了这莺儿,养在笼里给哥哥当个伴儿,他可会好些?
要拘我?不可再留在这里,我飞开去。
莺儿……底下,雪鸿不答,却忽然戚了眉,低吟一声,好像直觉一般,我忽然疑心她知道些什么。难道是她?可是为什么呢?绕来绕去,我总找不到一个有理由要我性命的人。但雪鸿,真是知道什么的样子呢。
她最后那声“莺儿”是什么意思呢?她想到了什么?会和我有关系么?不管怎样,我已料定了她知道些什么。
府上前后寻了一圈,见着老爷夫人,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老爷好象老了很多。夫人更是心事重的样子。两人却不多言语。那么也是因为少爷的病了。到不曾见着那少爷,我甚而不知道他的厢房在哪里呢。不过罢了,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么?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竟有些气短,冥冥中我竟开始觉得这两桩事情关联起来,只是摸不着是在哪里搭上的一环。是因为雪鸿的那一声“莺儿”么?说不清楚。
也没有寻找庆儿。不论如何,我决意留心着雪鸿。
黄昏时候,暮色重重的垂落下来。雪鸿去给老爷夫人请安,我跟了去。我已晓得要好好隐蔽自己,不可再让人家瞧见,要真被碧霓拘进笼子,我用的这些功可就都白费了。
老爷好像都无心应付这些礼节,挥了挥手,仍是没有言语。夫人却象得了什么安慰,虽眉头未见舒展,望着女儿那种眼神却是彼此心意相通的。不再是白日里那种有苦无处说的样子。那么,有什么事,是她和雪鸿守着的?连老爷都瞒着的样子呢,会有什么事情都不能告诉老爷呢?
也好,我且等她们私下说话的时候。两个女人知道的事情,我总不会等太久。
果然,雪鸿回了厢房,不过一盏茶时候,夫人也来了。
却是先四顾无人,关紧了门窗。我有些心急,怕听不清楚说话,也愈发奇怪起来,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要这么私密?仍是在窗纸上啄了小洞,凝神静气去听去看。夫人那些心事是真的压得很重呢,急急要倒出来。只是声音之轻,我只听得个大概。
哎,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做了这样的事……她道。
总不能让老爷知道了原委,要不然,非气煞他……又道。
给他速速娶了媳妇或者会好,但人家虽看重知府的地位,却也不会把好好的女儿嫁给傻子啊……
娘,不要这样说了,也是冤孽,雪鸿一直沉默的,终叹了一句。
这一句到把夫人激得爆发了,什么冤孽?分明是那妖孽!我早说你爹……雪鸿忙劝,夫人的声音又倏的小下去。
我不曾听得那关键的话,可是奇怪了,分明是少爷的事情,怎么又扯到老爷了?妖孽?什么妖孽?
娘,事到如今,只好再差人去寻些好大夫给瞧瞧了。你不可动了肝火伤身体,爹那头要瞒着,哥哥这个样子,碧霓又不谙事,你切不可以再伤了自己。
可是雪鸿,雪鸿,你不知道,你爹那头,我怕是越来越瞒不住了呢。一向端庄稳重的夫人,竟有一种似要崩溃的样子。那逆子的病愈发重起来,不住说些胡话,我怕你爹……
娘,我拦着爹和碧霓,不让他们去多探,放心娘。
雪鸿,我这心却仍是安不下来啊。官府那头虽说搪塞过去了,有碍着我们家的地位,不会再查,但毕竟荒唐得很,我又怕那些拿了银子的人不牢靠,透些什么给你爹,还有那个庆儿,打发得也总有些不明不白……
她不曾说完,我已经不能呼吸,庆儿?庆儿?是伺候我的庆儿,原来她是给打发了,可是,这岂不是说,这些事情,都是和我有关的了?我再听不见她们后面说些什么,好似天旋地转一般,很多模糊的心绪粘贴起来,似有了形状,却仍是说不清道不明白。
竟是那个少爷么?为什么呢,没有一点点关联的,我甚至记不得他的长相,不曾想过要去他那里打探些什么,便是知道他病了,也一直不相信会和莺娘有什么关联的。可是,听夫人和雪鸿的话,却分明是他啊。他是因为杀了人心慌而害得病么?可他为什么要来杀我?无冤无愁,无缘无故啊!
我终于寻到他的厢房。灯已熄了。明日天明,我要探个明白。
我不曾久等,在院里那株桂树上栖了一宿,他起的也早,也不做事,到了庭院里痴痴立着。
生前死后,我第一次端详他。一袭素衣的公子,若不是憔悴的紧,倒真是当得起那句“貌比潘安”。那么往日听得那些说溢美之词,或者也不是空穴来风。不过是眼神那个空,真的是失心疯呢。谁怨你,要无缘无故杀人呢?你是为什么?你说啊。
却见他从衣襟里取出一方白缎,痴痴握着。天,我认得那上面,那一双的鸳鸯,那是,那是我的啊,元宵那一日,我未绣完的鸳鸯枕!还有那不能洗尽的淡淡血迹,那是,那是我的!禁不住,啼出声来。
叫他发现了。那没有神采的眼睛将敛未敛,好似落到我身上来。
莺娘,一顿,接着竟是这样叫。
我大惊,几乎落下枝头来,他能看破我的真身么?才想起他是发了痴说的胡话。不再怕了,索性站稳。到要看看他说些什么胡话?
莺娘,他的眼神分明仍是散的,却能朝着我走过来,你,你,你为什么做了爹的侍妾?嗫嚅半晌,竟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我如遭雷击。
他不留意,尽自道来,那一日跟了爹出门,见你在溪边浣洗衣裳,虽一身粗布衣裳,却掩不住巧笑倩兮,是多少富家小姐都没有的纯澈之美啊。虽是初见,我心里已是欢喜。却不想三日之后,你竟被爹爹娶进门来,做了我的二娘。二娘?二娘?你的年岁都不如我,竟是我的二娘。
你是不曾看过我一眼的,我这个名分上的儿子,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是只顾了伺候好我爹爹的,却不晓得我日日见你,心里都是怎样的乱。你是那般守礼贤淑的女子,便是娘那般刁难,也一直默默忍下,不曾申辩些什么,你或不觉。可我心中,这却都是灼灼的痛啊。若不是我爹,那日,若是我……
我看到他那种失心一样的眼神,陷于一种不能思考的麻木。
可是晚了,晚了,都晚了,你进门那一日,我就知道晚了,那一重身份之隔,是永渡不过的,两年,整整两年时间,没有人知道我的煎熬,我借酒浇愁,几不能自已,幸而不曾说了太多的疯话,传出去的,只道是爹的好福气。呵呵,爹?为什么总是爹?总是他和你连在一起,不可以是我?
莺娘,我忍无可忍,我怕啊,我怕如此下去,会使你我更加深重的不幸,你却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依旧那样忍让的侍奉爹爹,呵,你幸福么?你没有幸福的,娘容不得你,爹又听娘的,你怎能幸福呢?罢了罢了,不能给你幸福,就让我给你解脱吧,你解脱,我也解脱,好不好?好不好?
元宵日,若不是爹,我们或可以携手上灯,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可是却……好了,就是那一日了。我心里明了,在你的别院外面侯了半夜,只等庆儿出去。
可是我悔,莺娘,悔自己下手太快,都不曾让你回头,我该让你回头的啊,好让你记得我,结果却是,你或者到死,都不曾在意过有我这样一个人吧?可是,莺娘,我却是一直,一直一直爱着你的啊!
原来,便是你死了,我也终无法释怀的啊,只有陷得愈深啊!
呵,呵呵……多情应笑我,呵呵,……
他干笑起来。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真的疯了,竟伸手过来轻轻抚摸我的脊背。
我再无法也无意飞走,望定了这个人,我眼里该是燃着火的,说什么爱我?荒唐,倒是取了我性命是真,好了,你是我的仇人,现如今就站在这里了,我的面前,我终可以恨你,可以报仇,可以甘心!或者我该笑吧?象那日在阎罗殿上,我什么都不曾做过,却成了夫人嘴里的妖孽,却要遭你这般莫名的爱,莫名的杀!
可不知为何,从心底涌出来的却是泪。
他那些毫无道理的荒唐话,为什么竟叫我心里微微发热,没有办法去怀疑?他那曾经握刀杀我的手,为什么竟是暖的,叫我的羽毛颤抖起来?为什么他那面孔上,竟不见歹人的凶狠,却是一种凄凉的好看呢?
汹涌如潮的泪,泪?鸟儿也会有泪的么?而他,看得见隔着阴阳两界流淌出来的泪水么?
兀那女鬼,你即已知害你何人,我当为你主持公道。
才发觉又已站在阎罗殿上。却不知如何去面对那个期盼已久的结果。造化弄人么?让莺娘一世都为了别人活着,有一天死在这个冤家手里,却得知命运原本可以有另外一重安排的。
原来,原来这世上还有人在意过莺娘,却又是一个无法去争取的人,只晓得要毁掉自己得不到的。
你说莺娘的那些好处,是莺娘自己也不曾晓得的,莺娘哪里会晓得,向来都是没有人会真正在意莺娘的啊。是以莺娘死后,才会这样不甘,这样不甘,几近怨毒,非要闹个明白,可明白了,却再也解不开了。
你说莺娘从不曾望过你一眼,从不曾想过你什么,其实,莺娘何曾想过什么呢?只是收一个侍妾的本分而已啊,莺娘哪里会有这样的念头,莺娘一世,都不曾妄想过可以去想什么人,去欢喜什么人,去,爱什么人啊。幸福?那是你们才有的奢侈,与莺娘,那笔能给娘看病的聘礼已是最大的福祉了。我是不敢有奢望的人啊。
再说了,你不也一样是不可以跨越规矩礼教地位身份的人么?宁可摧毁,没有办法渡过。
于是,生死两隔,你生生酿成。你怨不得阿!
恨你,夺我性命;却亦有一丝莫名的温存,无从下手。
莺娘啊莺娘,你是不甘心的啊,却怎的变成这样……
哎,空自长叹,终无法回答那一声问。
兀那女鬼,我即刻便索了那歹人性命来。
罢——了——,我当欢呼,却听得这两个字从心底传出来,似乎不曾思考过,原来已经决定了。
罢了罢了,现如今那失了神志的人,早已不是那风流倜傥的公子,早已不是那程家单传的骄傲,他已遭了报应了,他欠我的,便也算还了吧。
罢了罢了,阎王老爷,前尘往事,莺娘已经无意……不知为何,竟语不成声,一世不曾复杂过的人,却再入了地府以后明白纠结心痛,也不是什么好滋味啊。
罢了罢了,只求喝了孟婆汤,速速忘记,不再受其扰。
阎王竟也沉默,难得你也是个有气度的女子,来世,不会再受苦。良久,曰。
我无语。
那一年,杭州城里好像有传说不尽的谣言,都说知府家里中邪,先是程老爷的侍妾莫名挨了刀子,然后独苗的大少爷又发了痴,不晓得什么毛病,恍恍惚惚二月有余。忽一日好像好转起来,却是回光返照,不一忽儿便愈发恶化了。不会说话,双目空洞,只道吃喝。是失了魂了。
有人说,那是程知府为官不仁,遭了天谴要他们绝后。
亦有人说,程妻黄氏为人狭隘,逼死了那个侍妾,结果侍妾化鬼勾走了少爷的魂报复……
不一而足。
然有些话是终没有传出来的,譬如,少爷忽然病重那日,难得获准去探望的二小姐碧霓,曾见着少爷厢房前的庭院里一只死去的鸟儿,轻叹一声。
呀,这不是前日里见过的莺儿么?怎的就死了?可惜了呢。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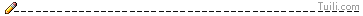
|
一点新一点旧,
一点光一点影,
一点等待一点蹉跎,
岁月流转,原来,不过如此……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