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麻子(十麻子) 十麻子(十麻子)
|
|
|
1 楼:
十麻子探案之偷窥
|
03年04月21日16点22分 |
偷窥
庄伯穿过平房的小院时,穿红格衬衣的女孩正在围墙边的水龙头旁准备接水,龙头打不开,弯腰用双手拧,从表情看,用了很大的劲,龙头还是拧不开,女孩子直起身来。嘴角嘟囔了几下,满脸不快乐。
庄伯对她笑了一下,表示了对外来人初次见面的友好,说:“龙头打不开?”,女孩子点头,斜着眼打量他,庄伯上前帮她拧了一下,还是打不开,说:“龙头坏了,有扳手吗?”女孩说:“没有。”庄伯这才注意,这女孩短发,二十一二岁,中等个子,不算丰满,但也还算漂亮,脚上的波鞋有点陈旧。
转身从家里拿来了扳手和一个新龙头给她换,笑了一下说:“我一个人住隔壁那楼。刚从家里来?” 女孩扭头看了一下身后,说:“是。”庄伯今年六十一岁,很喜欢和年轻女孩子说话,这让他觉得很快乐。他还想问她多一点的情况,一个左脸上有块疤痕的男人走了出来,插在了庄伯与短发女孩子之间,两人一起把坏龙头换了,庄伯觉察出他故意是横在中间提防他们说话的,问:“她是你女朋友?”疤脸说:“不,我们是老乡。”庄伯觉得疤脸干这些活,手一点也不灵便,但力气还是很大,疤脸向庄伯道了谢。
庄伯希望能被邀请到他们家里坐坐,他是个很喜欢与邻居往来的人,但他们没有。
疤脸对那女孩说了几句,女孩低头进了屋,从窗户里往他们家里看,床上还睡着一个女孩,散开的长发遮住了半边脸;屋内的行李很简单,桌子,床,几个行李箱。庄伯几次提问,他都回答得很简短,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不知道该问些什么了,觉察到了他们并不欢迎他,只好从院子后门往芒果园走去。
庄伯突然发现,围墙边的小树丛后还有双眼睛在瞪着他,——是一个留平头的男人,宽宽的肩膀,把大腿紧绷的牛仔裤,底很厚实的陆战靴,从庄伯身后走了出来,跟疤脸说了几句话,庄伯感觉两人一直在身后看着他,疤脸对着庄伯的后背说:“明天买一个新龙头还你。”庄伯说,“不用,我们是邻居。”
正是芒果花开的季节,谈黄的、细碎的芒果花,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忙碌的蜜蜂在花上嗡嗡嗡,但庄伯无心看这些,心上也象芒果香气一样浮动着一丝不祥的预感:刚才三个人对他的明显的紧张与不安。
这里是在深圳市市郊,自港商在他们村办了很多工厂后,这附近的很多村民都搬到靠国道旁去住了,这里成了空心村,不远的大芬村是有名的油画村,有上千名画家租在那里画画,然后卖画给上门收购的港商,所以偶尔会有画画的年轻人来这里租住。他隔壁梁洪福的那套平房,自上次那个蓄长头发、绘油画的年青人搬走后,空了好几个月,两天前搬来了这几个,庄伯怀着友好心情去结识新邻居,但新邻居们对他显得很戒备,没有看见绘画的用具,肯定不是画画的。
疤脸为什么要提防他与女孩子说话?疤脸说与短发的女孩是老乡,鬼才相信,老乡在一起当着外人说话会用普通话吗?而与平头却讲了一通听不懂的土话?而平头为什么又要鬼鬼祟祟的在暗中窥视呢?刚才走的时候,几乎感觉到平头野兽一样的眼睛盯得后背火辣辣的痛。所有这些像毛毛虫一样的撩着他的心,他想,一定要查过究竟。
两年前老伴去世了,庄伯现在一个人住在那栋两层楼小楼里,儿子办了一家公厂,家搬到新建厂房的顶层,几次要求他搬过去同住,他不同意,屋后是他家的一个芒果园,他想现在虽然经济好转了,但农民的本份还是不能丢。庄伯脸膛红润,身体还很好,独处久了,对外人就怀了极大的好奇。
芒果的花势不错,庄伯转了一圈后,回到了家里,是套独立的两层小楼,大门是双层厚实的防盗门,女儿提醒过他,现在深圳的流动人口很多,在家出家都要把所有锁都上好。
庄伯在想,两个男人是一路,而那短发女孩跟他们不是一起的,第二天,平头男人真的还了个新水龙头来,寒喧后庄伯故意眯着眼睛问:“短发女孩子是你女朋友?”平头说:“不是,是疤脸的女朋友。”这让庄伯就觉得更奇怪了,平头与疤脸说的不一致, 那么那短发女孩子到底是谁的女朋友?
这激起了庄伯极大的兴趣,爬上了小楼的二楼,有一个小窗户正对着那个小院,在窗帘后,很适合偷窥。庄洪福的这套平房整共是三间房,外加一个小院,在院子里的活动,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两天的观察,还觉得这四个人中间真有问题:平头说短头发女孩是疤脸的女朋友,但有一次却平头搂着她的肩坐在床上,而又有一次疤脸把手伸到短发女孩子裤兜掏东西,这又是为什么?到底是谁的女朋友?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还有那长头发的女孩子很少露面,好象跟他们三人不合群,住了这么久,几乎还没有看清楚过她的脸。他们每天早上很晚才起床,好象什么都不做,但一到晚上,很早就熄灯了,平房里静悄悄的。这些疑问就像浮标一样在庄伯心里上上下下,扰得他整天都不得安生。
第二天早上,庄伯骑摩托到村头的茶馆去喝早茶,这里是村里的新闻集散地,张家做寿、李家嫁女、刘家生子,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第一手的快捷信息,但今天,大家都在热烈的谈论这近几天发生在村里的几启抢劫案,劫匪中有男有女,昼伏夜出,屡屡得手,在村里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庄伯敏感的神精被触动了,那四人的行迹不就很象大家谈论的劫匪吗?
庄伯心里庠庠的,骑着摩托在村西的大榕树下碰到了治安队长罗四,罗四左臂上带着个红箍箍,正在巡逻。庄伯没有在村里的治安队干过,但当他年青的时,国民党特务在沿海搔扰频繁,在罗四的父亲罗老支书的带领下,扛着梭镖在村头放哨,所以警惕性还是很高。
庄伯对罗四说有一些话事跟他说,罗四好象听出他话中有话,郑重的把庄伯领到了家里,泡上了功夫茶,罗四等着庄伯说。浓郁的茶香升腾了起来,话到嘴边,庄伯又犹豫了:只要自已一把怀疑说出口,治安队就会去梁洪福的小院里去抄查,自已的预感会不会有错?在深圳男女合住在一起的情况也是很多的,梁家与庄家以前就因宅基地打过架,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和好了,但是有点言和意不和,如果说错了梁洪福一定会认为自已害他,村民们也会把他的敏感当成笑话来,自已几十岁了可不想被人笑话。
话到嘴边,庄伯又犹豫了,跟罗四阿哈阿哈的干笑了几声,说自已是想到他家来喝喝茶、看看老支书,罗四有点不相信,但也没说什么。
下午女儿女婿来看庄伯,大奔抢眼的停在大门前,女婿是邻村的村长,眉飞色舞的讲了他们村治安工作的群防群治,在群众的举报下,打掉了几个犯罪团伙,派出所所长在庆功会上给他带了大红花,他说庄伯的村时也应该群防群治,打击犯罪。庄伯嘴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忍住了,女儿走时,又仔细检查了庄伯家的防盗门窗。
晚上,庄伯听到了隔壁的院子里门窗响动,蹑手蹑脚地爬到了小窗前,把耳朵贴到了窗户上,好象是有人出去,小平房没有开灯,黑影魅魅的,庄伯睡不着了,干脆把床搬到了小窗户下,一听有声响马上爬起来看,过了很久,迷迷糊糊听到了有人回来,好象还搬来了几个大袋子,接着又有人出去,庄伯竖着耳朵细听,到窗外透出微光的时候,再也撑不住,昏头昏脑的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太阳光射到他的床头。庄伯一起床,就骑了他的小摩托车去村头喝茶,村民们在议论得热火朝天:前段时间经常搞偷盗的那个小团伙,昨晚被罗四他们在巡逻的路上迎面碰上,手上都提着袋子,当场抓获了一个留平头的男子,两女一男跑了。
庄伯不等茶喝完茶,急急的赶到了村委会,治安队长罗四还在,通屑未睡,两眼通红的打着呵欠,罗四确认昨晚下半夜是当场抓获了一个盗窃的小平头,还有两女一男跑了,庄伯提出要看看贼匪,罗四说,刚带走,送到派出所去了。
庄伯有点失望,又急匆匆的开摩托车回了家,假装去看屋后芒果树的样子,慢慢的穿过那小院,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了,静悄悄的。又细心地等候了两天,疤脸他们还没有回来,庄伯终于确定这四个人就是那个盗窃团伙,暗自懊悔:自已早就发现这些人的不正常,为什么不去向罗四检举?如果这样,派出所所长就会给自已戴大红花,所有村民在台下看着自已,实在是件很风光的事。
该割蜂蜜了,庄伯爬上了小楼的楼顶,今年的芒果花势好,一箱就割出了十几斤好蜜。庄伯伸了下腰,吓了一跳:平头他们四人又回来了!不是被抓进派出所了吗?马上骑车去找罗四旁敲侧击的询问,罗四确认:平头还关在派出所里,另外逃跑的两女一男也被抓到了,正在立案侦查。庄伯有点很失望地回了家,路上暗自庆幸:开始就觉得这四个人也不怎么像坏人,幸好没有乱说,要不,一定会成为村里的笑话,如果那样梁洪福也一定会认为自已是暗中害他,梁洪福办工厂欠了一屁股债,很在意小平房每月的这点租金,好险!
不只是平头四人回来了,他们还带来了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年青人,庄伯有意给疤脸送了点蜂蜜过去,顺便问这两个男人是谁,疤脸说是他表弟,要住一段时间才走。
他们还是没有邀请庄伯到家里去坐坐,相反平头出来的时候还把门给带上了,长头发女孩子的脸在窗前晃了一下,很快消失了,庄伯没怎么看清楚她的脸,好象是柔柔顺顺的样子,难道她怕见生人吗?那两个是他表弟吗?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说要住一段时间的两个男人当晚走了!疤脸为什么又要骗他?
他们还是什么事都不做,但每天都有陌生的男人来,有时一个,有时两个,一来就把门窗帘关得紧紧的,过不多久,又开门走了,疤脸好象手头还很宽裕的,昨天还买了辆斩新的珠江摩托。
有男人来;关上门;还有钱。这些事情一整天都在庄伯脑子里转,突然醒悟:两个女人是妓女,平头刀疤是皮头客,怪不得他们经常说谎,整天神神秘秘的。一个月终于把这伙人琢磨出了个究竟,庄伯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把这情况对罗四举报?说几个男女住在一起;每天有陌生的男人来;有可能是做妓女的,——这又能算得了什么?在深圳几个男女合租在一起的很多,他们都有很从老乡、朋友。就是有这么一回事,罗四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左思右想,庄伯胸中那只忐忑跳动的兔子终于被按捺了下来,但晚上还是睡在二楼的小窗户下,注意着隔壁小平房里的四个人,蒙蒙胧胧中,被一阵争吵声惊醒,“辟啪”,是打耳光的声音,庄伯马上爬起来偷看,好象是疤脸在打长发的女孩子,没有开灯,打得很凶,“咚”的一声,是脚踢到了人的肚子上,接着听到有人倒地,还伴着有女人抽泣声,声音呜呜咽咽,哭得很伤心,也有点象是短头发女孩的声音,几次激起了庄伯的怜悯,但一想到疤脸的凶神恶煞的样子,这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庄伯不敢再多的想法,用被子捂着耳朵睡了一夜。
第二天,庄伯无聊中打开了电视,正在播放本地新闻,电视上铐了几个身形狼狈的男人,播音员解释说,打掉了一个拐卖、胁迫妇女的卖淫犯罪团伙,这伙人采用欺骗,引诱的手段从内地带了几个女孩到深圳,锁在出租屋里凌辱、强迫她们卖淫,画面上又放了几个女孩的照片,年龄都不大,可怜兮兮的,脸上都被打了马赛克,庄伯突然一愣:把女孩关在家里,胁迫人卖淫,疤脸这不跟他们一个样吗?疤脸昨晚上就打了她们,一定是她们不愿意,反抗,,疤脸和平头就用武力强迫她,凌辱她,这太象了,怪不得一开始疤脸就提防庄伯与她们说话,从不让庄伯进他们家,现在疑团都解开了,这样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普通的卖淫……
这样庄伯落地了的心又悬了起来,穿过小院去芒果园时,尽量装着目不斜视,但这天晚上,庄伯被“哇”的一声女人的尖叫叫醒,声音短而且急促,好象极其痛苦,接着就是长长的沉默,庄伯吓得祟祟发抖,又是钪铛一声,象重物敲在脑门上一样,是疤脸他们屋里在剁板上重重的剁东西,那东西好象很硬,剁了好久才剁下来,这么晚了又会是剁什么?平房里没有开灯,从小窗上看上去漆黑一团,庄伯吓得也不敢开灯,又隐约看见疤脸他们几人去了围墙后的芒果园,辟辟乓乓的捣弄了一通才回来,一晚上的睡眠也象粳米粥一样,醒了又睡,睡了又醒,断断续续。
第二天,庄伯在芒果园看到了一行血迹,延伸到了一株小芒果树苗下,庄伯的心跳了一下,疤脸无声的跟到了后面,对庄伯笑了一下,疤脸说,他们昨天宰了一只鸡,没宰死就从手上跑了,跑到这树下才死,撒了一路的血……
平头一伙还照常起得晚,但长头发女孩再也不见踪影了,庄伯装着很无意地问在路上碰到的平头,平头说,她十四号中午去东莞了,庄伯算了一下,十四号正是他们晚上剁东西的那一天,好象那天黄昏时候分明还看到过她的人影在院子里晃了一下。
庄伯现在一合上眼,梦里就会反反复复地出现那棵小芒树,树叶上没有一丝风,就象有一台摄影机对着那颗芒果树做360度的旋转,反反复复的出现,总才觉得那小芒果树苗有点不对劲,感觉被人移动过一样,没过两天还真的验证了他的预感——芒果树叶子突然干萎枯黄,庄伯心头一跳,把脑中的各种片断链接起来,编织出一个完整的情节:疤脸和平头把不她家乡的两个女孩诱骗到了深圳,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租下了一套房子,一开始来就提防女孩子跟庄伯说话,疤脸充当鸡头,强迫她们卖淫,后来女孩子受不了,反抗,不愿意,疤脸狠狠地打——那天晚上他亲耳听到,后来,长发女孩子还不曲服,——可能是试图逃走,疤脸或是平头就把她杀了——应该是失手杀死,因为他们还指望她给他们挣钱的,所以那天晚上他听到一声女人的尖叫,杀死后就把长发女孩子进行了肢解,——钪铛钪铛是剁尸体的声音,尸体剁完之后,就把她埋在了小芒果树下,人的尸体是世上最肥沃的肥料,小芒果树受不了人体的肥沃,被俨死了。
这些推理像座大山一样,压在庄伯的心上,让他不能呼吸视听,庄伯一辈子都小心瑾慎,不乱说一句话,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他是不会说出来的,他每天都要向芒果园跑上几趟,注视着这颗有点神性的、梦中向他暗示的芒果树,树叶开始脱落,飘飘荡荡的剽下,就象那长头发女孩子的生命在脱落,庄伯终于忍不住了,——他自信他的推理过程思考过上百篇,经得起任何推敲,他决定去给罗四举报。
“真的?”罗四听了后象触电一样地站起来,“你要确定,庄叔。”两只眼睛像两束光电一样的盯着庄伯的眼睛,希望能从他眼里看出点胆怯。
“千真万确!”庄伯一面说一面用右手在脖子上做了个砍头的姿势,“那天深夜我听到了在剁板上剁尸体的声音,第二天还看到了一行血迹。”说着,庄伯又把刚才说过的事情再重说了一遍。
“那好,我们先去挖开看看,一面打电话通知派出所。”深圳的治安队长是一村之望,罗四还从来没碰到过这么让他兴奋的事。
治安队几个人先把疤脸他们包围了起来,庄伯拿来了锄头,还指着隐约的血迹让罗四辩认。罗四点点头,指挥手下在小芒果树下开挖,开挖的情况还真让大家兴奋,芒果树下果真是刚被人移栽过,泥土很松,挖到两尺,翻出了一些带血迹的泥土,大家兴奋起来,接着翻出了一些鸡毛和一个公鸡头,再往下挖就是没有翻动过的实土了,庄伯说再挖再挖,一定是在更深的下面,坑越挖越深,罗四的脸色在一边越来越难看,庄伯也是急满头大汗,挖到最后,土越来越硬,治安队员把锄头一扔,再也不挖了。
罗四把平头领到了土坑边。
问:“这鸡头跟鸡毛是你埋的吗?”
“是。”
“你为什么要把它埋在这里。”
“我们家乡有个习俗,如果公鸡没杀死从手上跑了,是不吉祥的,要把它的毛跟头埋在一颗树下……”
罗四把鸡毛往庄伯脚下一扔,“庄叔,你的好千真万确,我今天的脸丢大了。”眼睛狠狠的横了他一眼,带人走了。
一连几天,庄伯不敢再去村头的茶馆,他想他的故事一定被村民们传唱成了一首歌,几天也不说一句话,但庄伯不承认自已的判断错了,那天晚上,他明明听到了一声人惨叫、剁板剁响的声音,如果剁一只鸡,果真会剁得这么响吗?平头他们还是照常的过日子,在路上遇到庄伯也不显得特别生气,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庄伯认为这种奇怪的表情是对他一种冒似胜利的饥笑,那么自已的推理又错在哪里呢?庄伯百思不得其解!
村里的小孩发疯似的往国道边跑,庄伯不明所以,也骑摩托跟了去,国道边的草丛里,已围满了一大堆人,庄伯分开众人,钻了进去,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一具无头无手的裸体女尸,横躺在草丛里,几个穿白大褂的警察,正在堪查,罗四和村里的几个治安队员也在一边帮忙。尸体可能被遗弃在草丛中已有一段时间了,有风吹过,一股恶臭扑来,围观者纷纷掩鼻后退。这具尸体很丰满,看上去还很年轻,过子也比较高,单单就是没有了头。
后来听村民们传述,警察鉴定后说这具女尸大概是十四号左右被害的,因为无头无手,死者的身份一下难以辩认,庄伯紧绷的神精一下子被触动了,为什么凶手偏偏要砍掉头和双手呢?不正是怕被村里的熟人辩认出来吗?尸体的死亡时间不正好与小平房里的长头发女孩那晚失去踪迹的时间相吻合吗?庄伯一边这么想,一边又有意无意地又穿过了那小平房的小院,往他的芒果园走去,小平房门正趟开着,只看到疤脸一人坐在屋里的橙子上,见庄伯走过,疤脸脚不自然地在脚下的方砖上跺了跺。
上次罗四他们挖的坑还没有填好,鸡毛还分散在四周,对着曾让他感到耻辱的现场,庄伯又沉思了起来,庄伯认定,国道边草丛里的那具无头女尸就是那个长发女孩子,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把鸡头埋在这芒果树下呢?人头又会被疤脸他们埋到哪里去了呢?庄伯想起了刚才疤脸无意识的在方砖上的跺脚。又一个想法在他脑子里逐渐形成。
人在做了坏事后,心里总是不踏实的,总会是在猜想,有人在注视了着他,奥!对了,就是这样,自已差点上了疤脸的当。
一些片断又在庄伯脑海里编成了一个连续的情节。
——疤脸一伙那晚失手杀了长发女孩子后,剁掉了她的头与双手,让她面貌难以辩认,然后脱光她的衣服,把她抛尸荒野,他们知道尸体一定会被发现的,怎样才能不被引起怀疑呢?,那就该先被别人搜查一次,但搜查到是埋在树下的鸡头,这样就会记永远解除对他们的疑窦,那么人头与双手会被他们藏在哪里了呢?肯定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地方,疤脸一定知道我去看过女尸了,不由的在方砖上跺了跺脚,难道不会就被埋在砖下……?
庄伯猛跺了一下脚下的泥土,下定决心,又骑摩托车往村尾会开去。
村里出了案子,人出出进进的,治安队的办公室里显得很乱,罗四坐在椅子上正在与一个秃了顶的港商谈话,早就看到庄伯来了,眼睛乜了他一下,又接着跟港商谈,没完没了,“咳!”,庄伯咳嗽了一声,想插话,罗四做了手势,阻止了庄伯的发言,庄伯坐在一边,屁股有点痛了,把体重由左边屁股换到了右边屁股,接着又换到了左边,连换了三次,罗四与秃子港商终于谈完。
“咳,庄叔,”罗四从嘴里吐出一口浓烟,手上也给庄伯递上了一跟烟,“是不是晚上又听到不明的剁剁板的声音了?”说着,嘴角露出了一丝饥笑。
“噢,是,是……也没有。”庄伯现在在才知道,罗四刚才是故意让他坐了这么久的冷板凳。
“唔!那好,我以为您又要让我们去给您挖芒果园了,庄叔,那次队员们在您的果园里手都挖酸了,到今天都还有人在抱怨呢……”
庄伯都记不得自己是怎样在罗四的饥笑声中逃去那办公室的,只知道罗四以后完全把他的想法当成一个玩笑了,这一切都怪疤脸,自已一不小心中了他的套,看他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一定是这一伙人里面的头头。
晚上,庄伯又被女人的尖叫声惊醒,这一次是在打那个短头女的女孩子,短发女孩逃到了小院里,被追得团团转,叫声凄历,庄伯想到,那个长头发的女孩子就是在这么一个晚上被打得失了踪,后来,荒野里就有一具无头的裸体女尸。正是因为这事,自已还被弄得在村里没有了一点地位,庄伯一直认为自已的推理没错。紧接着,庄伯听到了打门声,一个女声在叫“救命,救命”,庄伯突然想:如果自已把这个短女的女孩子放进屋来,把一切都问清了,无头女尸的案子会解开,以后自已在罗四眼里也不更有分量了吗?
庄伯起了床,把防盗门上的四个栓一个一个的拔开,刚开门,轰隆一声,一件黑乎乎的大物砸来,自已马上失去了知觉。
等他恢复知觉的时候,发觉自己已被五花大绑了,嘴上被封了一张大大的胶布,家里已被翻箱倒柜。
“萍姐,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我们找出来了。”庄伯的眼只能望着天花板,听出这是疤脸的声音。
“笨蛋!”听到有人在疤脸脚上踢了一脚,“老鬼嘴里不是还有一颗金牙吗?做小弟都不会做。”庄伯脑子里一阵迷乱:这女人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柔柔弱弱的。
紧接着,天花板上晃过来了一张脸,是那个长头发的女孩子的脸!狞笑着,撕掉了他嘴上的胶布,一双手鬼爪一般的往他嘴里探来。
“我们在这里潜伏了两个月,终于把这个老东西搞定”
长发女孩子不是变成了那草丛里的裸体女尸了吗?原来她没死,观察了这么久,一直在猜想疤脸一伙在害人,原来他们真正的是想害我。
这些就成了庄伯有生之时的最后意识。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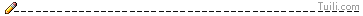
|
|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