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nfanglai(丁甲) linfanglai(丁甲) 
|
|
|
1 楼:
风雨夜
|
03年08月25日14点41分 |
风雨夜
回到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外面下着绵绵细雨。我喝得晕乎乎的,一路撞到门口,摸出一把钥匙,捅了好久才将门打开,我的心头浮起一股快意,于是我听到从自己的嘴里发出一阵嘿嘿嘿的怪笑声。
房子里黑乎乎的,可是在酒精的催化下,我的感官却异常敏锐起来,似乎平常被压制在身体深处的东西,这时全都探出了脑袋。而且我对这房子是那么的熟悉,打我生下来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我都没有长久地离开过它。房子里的摆设,也总是简单而古板,因此,虽然我踉踉跄跄地,却也没碰翻任何东西。我懒得开灯,径直往楼梯扑去。
我听到自己的脚下发出吱吱的响声来。这个该死的楼梯,差不多八九十年了吧,大概从来就没有换过,还有二楼的地板,也是老掉牙的古董了,其实这整幢楼房就是又矮又破又旧,老早就该送进火葬场了,可是我老爸没能力修补它,传到我手里,一样也没能摆脱这具僵尸的束缚。
二楼只有一间卧室,是我和妻子的。我们还没有孩子。结婚快六年了,我还是不敢要孩子,我怕养不起。妻子总是埋怨我,可我有什么办法呢?
卧室里同样一片漆黑,妻子老早就睡下了吧。我摸到床沿,正要坐下,忽然“啪”的一声,床头的台灯亮了。妻子从床上猛地弹起,拿两道凶猛的目光钉着我。
“你还没睡啊?”我开始脱衣服了,也顾不得身上的酒味了。
“你还晓得回来?”妻将我一推,扯开了嗓子。她的嗓子一扯开,外面的风声似乎也变大了。
“深更半夜的,吼什么吼?”我没好气地说。
“你也知道是深更半夜了?你这野鬼,又死到哪里去赌钱喝酒了?”妻子的嗓子越发亮了起来。这一点我倒是早已习惯,结婚五六年来,也不知吵过多少架了。我的嗓子没她尖,所以总是输得多。一般来说,我忍一忍也就算了,不过有时候真的把我惹毛了,少不得也批她几个嘴巴。骂是骂不过她了,可论打架,她没我力气大。
今天晚上我的心里头不是很痛快,因此一上来也不甘示弱,回顶她一句:“管你屁事?”
“管我屁事?”妻子从床上跳了起来,“我这是为谁来?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她这么说其实也没错,我一时找不到辩驳的话,于是扭过头去不理她。床头柜上摆着一盘水果,我顺手抓起一只梨,又抓起旁边的水果刀。我看见小垃圾桶放在前面一只小矮凳的边上,就过去坐下。垃圾桶里掉着几卷梨皮,还有几个梨核。
妻见我不说话,又安静地专注于削梨,对她的话不理不睬,更是火冒三丈,冲过来一把打落了我手中的梨。这时,我也火了,嚷道:“你发什么神经?”
“我发神经?我看你才真正有病呢?”妻吆喝着,“成天只晓得赌钱,也不想想家里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家里是什么情况用不着你来提醒我。”
“那你说说看,你堂堂一个男子汉,你都做了什么?”
“我没做什么?我没做什么你有饭吃?你有梨吃?”我正弯腰把梨捡起,这时候忍不住就朝她脸上掼了过去。
“啊!”妻慌乱中叫了一声,“谁要吃你的饭?谁要吃你的梨?我要不是瞎了眼,当初怎么会嫁给你这种男人?”
妻的话严重烧伤了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刚才喝下去的酒劲这时猛地涌上了我的脑门。我冲过去一把抓住她的衣服,怒道:“你是瞎了眼,你有本事,你嫁给百万富翁去!”
妻也挣扎着,一副不肯服输的模样,“我也不用嫁给百万富翁,我就是嫁给讨饭的,嫁给一只狗一条猪,也比你强些。”
妻子的这番话把我推到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极端。我只感觉我的眼睛睁得我的眼眶都痛了,我的牙齿咬得我的牙齿都痛了,我的脸完全扭曲了。妻子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一张脸,这时也感到害怕了,身子不住地发颤,抖索着说:“你……你要干什么?”
这个时候,我忽然想到刚才开门时那一瞬间的快意,我忽然又感到水果刀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刚才喝下去的酒水,像钱塘江的潮水一样扑了上来,我完全失去了往昔的控制。窗外的风雨猛烈地敲打着窗玻璃。
妻的惊怖也达到了极致,她的嗓子像爆烈了一般,“你……你……没没……”
妻倒下了,暗红的鲜血一阵阵涌出来,渗入了古旧的地板中。
我也倒下了,累得直喘气。我不知在妻子身上捅了几刀。在那一瞬间,所有的快意很快就消失了。“啪”,大雨撞开了窗玻璃,一阵狂风卷了进来,我清醒了。
我的身子不住的发颤,我几乎麻木了吧。可是,就在我觉得自己已完全失去思维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却接连闪过一幕幕往事来:童年的无忧无虑;爸爸妈妈对我的打骂以及他们脸上的微笑;爸爸妈妈死去时看我的眼神和他们干枯的手掌;工作后上司的漠然和神气颐指;同事们聚在一起时的窃窃私语和隐隐笑声;回到家妻子的种种抱怨和粗暴……我的眼泪终于抑制不住地滚落了下来。也许妻说得对,我这种男人!唉,我“这种男人”!
我不知道自己呆了多久,渐渐地,窗外的风雨声也小了。我才想起,我该如何处理这后事呢?
刚才妻子大叫了起来,幸好周围没有什么邻居,外面又一直下着雨,又是深更半夜的,应该没有被人听到才是。我得赶紧将尸体处理了。我是没什么亲戚朋友,但妻子的家人总会问起她的下落的。该如何解释呢?对了,就说妻子晚上出来找我,遭了抢劫,被杀了。我还要显出十分着急的样子来,对,就是如此。
我的身上又增添了一股力量。要处理尸体得趁现在。我给妻子换上她平常的衣服,然后就抱起她的尸体,乘着夜黑出了家门。我家附近就是山区,十分僻静。这个时候,路上正是一个人也没有。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妻子扔进了山里,又摘走了她身上的手表、钱袋和戒指。
回到家,差不多四点种了。我累得近乎虚脱,连楼梯也爬不上去了,而且我也不敢再睡到那间卧室里去了。好在一楼还有一间客房,就在二楼卧室的正下方。我推开客房的门,拉亮了电灯。客房的布置十分简单,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不过平时都很干净,床上雪白的床单整齐地铺着。
我一下子就倒了下去。可是我依然睡不着,脑子里不停地闪过刚才那可怕的一幕。我的眼睛盯着天花板看,上面有一滩黑色的污渍。我想,这是妻的血渍吧,明天我一定要把这一切都清洗干净,绝不能留下任何的痕迹来。
忽然,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浑身打了个激灵。“不对,不对!”我叫了起来,一个可怕的想法像一道闪电,刹那间将我的心脏击得粉碎。
有什么不对呢?到底哪里不对呢?我的全身哆嗦了起来,我的牙根不停地打着冷战,我竟完全不能令自己冷静下来。
天花板上有血渍,这些木板又是那么的老久。妻子死的时候流了一大滩的血,这些血在开始的时候应该会渗透下来滴落下来吧,那么床单上就应该有血迹啊!可为什么没有呢?
难道说当时床上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是小猫吗?妻子是养了一只猫,可猫是不会再将床单整理好的。刚才的床单可是很整齐的啊。难道说……
还有楼上的那只垃圾桶,里面有几个梨核。我记得家中应该没有水果了,而且妻子一个人似乎也不会连着吃好几个啊。就算是妻吃的吧,按照她的习惯,应该是坐在床沿上吃的,那么垃圾桶就应该放在床边才是啊,可事实并非如此,垃圾桶是放在矮凳边上的,难道有人曾坐在矮凳上吃梨?是妻子坐在矮凳上吗?
还有,就是妻子临死时说的那句话,“你……你……没没……”没什么呢?是说我没良心吗?还是另有用意?
想到这里,我整个人完全崩溃了,我知道我再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了。然而也就在这时,我反而平静了下来。我下了一个决定。我慢慢地又爬到二楼卧室里,从我的枕下掏出一盒药瓶,打开盖。里面全是安眠药,这时应该还剩着好些吧。我每天都会为自己准备安眠药,因为自打成年以来,我几乎总是失眠,尤其是结婚以来,我的压力骤然变重了好几倍,我经常失眠,睡不着觉。
我将药瓶里的安眠药一股脑儿全都吞了下去,甚至来不及细数它的粒数。我又躺在了属于我自己的床上,往事一幕幕又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无忧无虑的童年;爸妈对我的打骂和他们脸上的微笑;爸妈临死时看我的眼神和他们干枯的手掌……
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好象要睡着了。一切都结束了,是啊,都结束了,终于……
第二天早上,一位年轻的女子惶惶不安地来到当地派出所,把她昨晚的经历讲给警察听。
“昨天下午,我提了一袋水果去看我姐姐。姐姐招待了我,姐夫出去上班了还没有回来。我们准备好晚饭等姐夫,可姐夫一直没回来。姐姐有些气呼呼的。晚上,我们在房间里聊天,一直到十一点钟,姐夫都没有回来。我回一楼的客房睡了。不知什么时候,姐夫回来了,和姐姐在楼上吵。我想这是他们的家事,我也不好插手,而且他们这样子吵架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也就没在意,只管自己装睡。后来吵闹声越来越大,姐姐还喊了我一声,可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听到楼上‘扑通’一声。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我忽然感到上头有东西连续滴了下来,滴到我脸上,粘乎乎的,还有一股血腥味。我再听没有姐姐的声响了,这才知道姐姐被姐夫杀害了。我很害怕,怕姐夫也把我杀了灭口,就躺在床上不敢发出一丝的声音,姐姐的血滴在我脸上,我都不敢移开一点位置,幸好姐夫好象并不知道我也在,并没有下楼来。我不敢点灯,黑暗中不知道过了多久,上面的血终于没有再滴下来。姐夫一个人在上面自言自语,说了好多。后来又说要怎么处理姐姐的尸体,还说要怎么撒谎骗过别人。再过了一会,我就听见他下楼了,一开始我很怕,以为他发现我了。后来才知道他是背着姐姐的尸体出去了。我见他去了一会儿,不敢再呆,就马上整理好床铺逃了出来。我姐那地方很偏僻的,当时又黑,又下雨,又是深更半夜的,又没有共车经过,我一路跑回来,差点就要昏在半路上了。”
很快,警方就组织好了力量,但是当他们赶到的时候,发现凶手已经畏罪自杀了。不过警方不明白的是,既然他还想着处理尸体,还想着撒谎骗人,为什么又会选择自杀呢?有人说也许是他后来又害怕了吧。这么说的确也没错,不过其间的前因后果,就没人知道了。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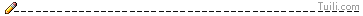
|
|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5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