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樱舞四方(林薰) 落樱舞四方(林薰)
|
|
|
1 楼:
窗外
|
03年11月14日22点44分 |
窗外
○ 落樱舞四方(=Glinrod)
(上)
凌晨两点半。已是深夜,天光却还很亮。天空呈浅红色,糅杂进了少许柠檬黄与淡绿,色彩很稀薄,显现出一种水样的感觉。云块清晰可见,缝隙间透出几缕黯淡的星光,孤独的射向这座城市。
办公室里虽然有人值班,但都睡熟了。夜光勾勒出这间没有开灯的屋子里的种种事物,使它们泛着一种奇异的光亮。就在这静谧的环境中,电话不合时宜的响了。
陈嫣猛的惊醒,迅速起身接了电话,周涛也从办公室另一头绕了过来,凝神听着听筒中传出的声音。来电显示屏上亮出了另一座城市的区号。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是等不及,还未等陈嫣开口便抢先发了话,是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是化学市刑警大队吗?”
“是的,需要我们帮助吗?”
“有人要杀我,求求你们救救我。”
“为什么不找当地警方?”
“他们不相信我,全说我是神经病,可我说的都是真的。”女子的声音开始变得颤抖。
“你能肯定吗?”
“当然否则我为什么要报警!”声音开始加入了愤怒的语调,颤抖也变得更明显了。
“有什么依据吗?”陈嫣继续问下去。虽然她也觉得这样不太好,但总是先核实一下为妙。
“有人跟踪我,并且当我在家时,有人会透过窗户往我屋里窥视。”
“你把这些告诉别人了吗?”
“告诉过亲戚。”
“谁?”
“我的姐姐。是表姐。”
“后来呢?”
“她也不信……你们来好吗?来我家。我想有些东西你们得看看。”
“你住在哪里?”
“云台山市清水桥北街四段十一号四幢五层西十六室。我叫沈海虹。”
天已基本亮了。
警车缓缓驶进那个院子,水泥路非常狭窄,车拐起弯来十分困难。四号楼前种了许多梨花,车身的震颤由车轮传给大地,又由大地通过树根,树干,树枝传给了梨花,花瓣纷纷扬扬的飘落了一地。春天马上就要结束了。
一共有四幢楼。楼体为东西走向,有十一层高;四幢楼按南北走向排成一字,四号楼在最北边。
周涛伸手按响了五层西十六室的门铃,但过了很久也没有人来开门。
“你们找谁?”一个声音在二人身后响起,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是管理员,一个中年人。在他看来,凡是在奇怪的时间有陌生人敲门,基本都不是什么好人。
“沈海虹。”
“哦,那你们……”土皇帝的架子略微放下了一些。
“我们是化学市刑警大队的。往常她这个时间在家吗?”
“在。她是装饰画家,在家里工作。”一看到革皮上亮得看不清形状的徽记庄严的嵌着,管理员立马矮了一大截,毕恭毕敬的气势直逼得人想往后退。
“她最近经常外出吗?”
“没有。这一周多以来她一直没出过门。”
“那有没有别人来找她?”
“呃……是有一个人来找过她,一个女的。”
“谁?你认识她吗?”
“好象是她的表姐吧……姓尉。”
“以前见过面吗?”
“没有。”
当周涛问管理员问题时,陈嫣又按了几下门铃,还是没有人来开门。于是,在问话的间隙,她低声对周涛说:“也许我们来晚了。”
周涛先愣了一下,继而又不情愿的点了点头,吩咐管理员:“你有房门钥匙吗?借我们用一下。”
管理员立马变魔术似的从一个窄小的口袋里掏出百十来把用一根尼龙绳串在一起的钥匙,分出其中一把,两个指头捏着递给了周涛。之后,他不安的看着周涛开门,随时准备着拔腿就逃。
门被打开了。
这是一套一室一厅一卫的房子,格局没有丝毫超凡脱俗之处,与其它相同型号的房子一样,普遍设计不合理——内室的门正对着大门,放眼望去内部环境一目了然。
只是此时,那道门像不幸被某个预言言中了似的紧闭着。
陈嫣已经嗅到了房间中游丝般漂浮着的异味,毫无疑问是从内室由门缝渗出来的。周涛先她一步冲至门前,握住转式门把手用力拧,想要推开门;但门已被反锁。他只得用肩背去撞门,门不结实得很,只撞了两下锁就坏了,他也因惯性跟着打开的门冲进了屋里。
一股猛烈的血腥味如放缰的野马般冲了出来。躲在陈嫣身后的管理员什么都没看见就先发出一声非人的惨叫,好象看见自己的尸体摆在地上似的。
由于周涛站在门口挡住了陈嫣的视线,因此她向前走了几步,周涛侧了侧身体,让她进入内室。
一扇镶着铝合金窗框的窗户正对房门,窗前是一张写字台,上面堆满了书报,桌角放着一台电脑;左侧是一张单人床和一个简易衣柜,床上零散的放着一副跳棋;右侧整一面墙都让书柜占了去,里面整齐的摆放着一列又一列书。一名应该是沈海虹的女子背对房门坐在转椅上,双手似乎是捂着腹部,弓着背伏在桌子上。
一切看上去都很安详,但如果把视线稍微下移一些,就会看到转椅底座周围那一大滩还没有凝固的暗红色血液。
“打电话叫大队人马来吧。”周涛吩咐陈嫣,同时又回头冲厅里化石般僵硬的定了格的管理员喊:“把门关上!不要让其他住户看见!”
周涛小心翼翼的把尸体翻过来,让她仰靠在转椅背上;陈嫣也收起手机,走过去帮他扶住椅子。
“死亡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只来晚了一点。”周涛摸了摸死者的胳膊,“尸体还很热,血也没有凝固。现在几点了?”
“五点四十。”陈嫣看看表,又把目光移向死者的腹部,见其双手紧握一把刀刃部分全部插入腹中的匕首,撕开了一处六,七公分长的伤口,周围有喷射状血迹。
切断了腹腔大动脉……她想。
“你跟他们说的什么?”周涛突然问,吓了陈嫣一跳。
“什么?”
“怎么死的。”
“没说,光说死了一个人。你觉得呢?”
“自杀?”周涛有些拿不准。
“不像。她刚给我们打了电话,心里有了着落,不应该自杀。而且……”陈嫣把刀刃部分微微拉出一些,“你来看,刀刃是单面的,朝下;而自杀……”
“通常情况是刀刃朝上。”周涛打断了陈嫣的话,环视了一下四周,没有任何打斗痕迹,“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你在这里找找有什么线索没有,我有问题问那个管理员。”
“好的。”陈嫣转身背对窗户,目送周涛出了内室进入小厅,又见他随手带上了门。
陈嫣靠在写字台上陷入沉思,不经意的扫了一眼仰靠在转椅上的死者,发现自己与那张因极度痛苦而扭曲的脸几乎是面对着面,不由得想起平日里那一沓又一沓的血淋淋的验尸照片,顿时一阵恶心,于是侧了侧身体,让目光避开死者。这下,她就完全背对着窗户了。
死亡时间在五点左右吗……陈嫣认真的想着,屋内陈设上看死者是独居,那么应该是外人进入作案了……她打电话时听口气应该是一人在家,这样的话就是打电话后凶手进入了……这个时间死者能为其开门的人定是非常亲近的人……蓦的,陈嫣想起了死者的表姐——这是个重点怀疑对象,不过,她似乎对她的表姐很信任……等等,我记得沈海虹打电话时说有人要杀她,那会不会是那个人?而那个人又是谁?“那个人”……“那个人”!
陈嫣真觉得有点绕不过来了。从电话上看,凶手应该是沈海虹说的那个跟踪她的人;但从现场来看——根据血迹可以判断,写字台前就是第一现场,凶手是趁她坐在转椅上背对他时出其不意的下了手,再伪装成自杀——而这样的话,凶手必定是个和沈海虹极为熟识的人,可是既是极为熟识,那就没有跟踪的必要了……
也许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案子吧……陈嫣想着,垂下头用力的眨了眨眼睛以驱赶睡意。本身就睡眠不足,又加上连开了两个半小时的夜间车,她已经很疲劳了。
蓦的,陈嫣觉得有人透过身后的玻璃窗在监视她,一种危险感同时出动了她的神经。
陈嫣本能的向前卧倒,伏在地面上,距离那滩血只有几公分之遥;与此同时,窗玻璃发出了一种异样的碎裂声,接着是子弹打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一朵小小的蘑菇云升了起来。
(中)
“.22口径步枪子弹……”闻声而来的周涛把那颗没打中目标的弹头捡起来放在鼻子底下从不同角度观察了半天,又忽然想起了什么,扭头问管理员:“有绳子吗?长一点的。”
“有!有!”管理员声音有点打颤,然后迅速转身抖抖索索的开了门,跑出去,带门时又弄出了巨大的声响——这大概是他平生第一次有如此刺激的经历了——先是刑警凌晨突访,再是完整的凶杀案现场,又是来自窗外的神秘枪击——虽然主角不是他。
“看见枪手了吗?”周涛问。刚进门时他被吓了一跳,由于陈嫣离那滩血太近,他以为她受伤或是已经死亡了。
“没有。”陈嫣轻轻拍打着衣服上的尘土,“我连是怎么回事都没反应过来。而且我当时是背对窗户。”
“你猜那会是什么人?”
“不知道。”陈嫣如实回答,“动机就更不清楚了。你想呢?”
“不知道是不是和眼下的案子有关。”周涛边说边瞥了椅子上的尸体一眼。
“绳、绳……绳子……”气喘如牛的管理员一头撞到门框,累得连举起手中绳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量窗户上的。”周涛接过绳子,自己拿一头,另一头扔给陈嫣。陈嫣应了一声,接住绳头,捏在手里,之后把写字台上的书报挪了挪位置,腾出一块一尺见方的空地,轻捷的跳上了写字台。她见周涛把他那头压在了地上的着弹点后,便把绳子拉直,右手拿着绳头停在了玻璃上的着弹点位置——这是一种简易的弹道测绘方法,但由于弹道呈一定抛物线,所以两个着弹点间距越大测绘精度便越低;刑侦方面常用该法寻找不明枪击现场的枪手大致位置。
周涛眯着一只眼睛沿绳子方向朝窗外看去。
“找到了吗?”陈嫣问。
“还没有……看见了,大约在对面楼顶天台上,顶楼西数第五扇窗子上面的位置。”周涛边说边站了起来,“刚才你站在哪里?”
“转椅左边,倚着桌子,大约在那本杂志的位置。”陈嫣见测绘完毕,便收起绳子跳下来,“刚好在弹道上。”
“那么说,真是冲着你来的了?”周涛有点不大相信。
“你的意思?”
“只是觉得有点奇怪罢了。你以前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吧?那么这就是初犯了。隔着玻璃会使射击精度降低不是吗?你来的时候天已经很亮了,为什么不那时开枪?”
“如果他想杀的是……不,假如他是想向警方挑衅呢?”
“那杀两个不是更好吗?如果他想挑衅,肯定想杀一人判死刑,杀两人也是判死刑,而杀两人效果更好一些。而且凭他的枪法,即使我们都在屋里,两个点射,我们俩还没反应过来就都完蛋了。”
“……”陈嫣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沉默了。
楼下传来了多辆汽车的发动机的噪音。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了单元门前救护车里停着的盖有白单子的担架上,沈海虹就在那下面沉睡,如童话中融化了的雪孩子般一动不动。她会记得是谁杀害了她吗?
陈嫣独自一人倚在一辆刷成蓝白相间并喷有“公安”字样的桑塔纳2000的一侧车门上,低头看着前方二、三米远处的地面发愣。二十分钟前,她被刑警队长罗加泉派下来看尸体,但明显的她的心思没有放在尸体上而是陷入苦思之中——先是两手交叉抱在胸前,过了没几秒又伸手抚了一下头发;抚了没半下,又把手垂了下去;紧接着又轻轻抓住了车门把手,同时又摇了摇头……如此折腾一番后,又回到了初始动作并不动了。
和煦的风在温暖的阳光下自由自在的飘荡着,吹得一树树的梨花翻起了波浪,又从中跃出一颗颗晶莹的水珠——那一瓣瓣洁白如美玉的梨花花瓣啊!随风纷扬着,又有几瓣落在了陈嫣身上,在缁衣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现在已是上午八点半多了,院子里的人们早已出门上班去了,留下了这空寂的院子和落寞的梨花。一个半至一个小时之前,曾有六、七十号人对四号楼前的这几辆警车和沈海虹的家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少则站五、六分钟,多则长达半小时,但最后都被上班时间的鞭子无情的抽走了。
再从头回忆一遍吧……陈嫣想,一开始,是在凌晨两点半,于化学市刑警大队的办公室中接到了沈海虹的电话,称有人跟踪她,顺便提到了她的表姐;五点半到达这里,进门后发现她被杀,管理员提到与她常走动的只有她的表姐,而且沈海虹很信任她;由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这应该是熟人作案;六点十分左右,我遭到了来历不明的狙击;之后便是大队人马赶来……如此说来,沈海虹的表姐最有作案嫌疑,但沈海虹在电话中提到的人更有可能是凶手,但这又与作案现场不符……也许……是有人逼着她打了那个电话?而且,后来的狙击又是怎么回事?很明显是冲着我来的,但周涛说得很对,也许那是一种保险心理?可又是谁开的枪呢?
两声明明没有却硬装出来的干干巴巴的咳嗽声传到了陈嫣耳朵里,她抬起头,见是周涛,便问:“怎么了?”
“罗队叫你去找沈海虹的表姐了解情况。这是地址。”周涛边说边递给陈嫣一张纸,“尸体我来看。”
街上人不多。作为化学市众多的卫星城市之一,也是最大的一个,云台山市的地盘与烟台市大小相仿,建筑却如青岛市的城区一样紧凑,并且多是美丽的林荫大道,新型的双层公共汽车与古老的有轨电车并行于其上,有着如同大连市一样的气质。
地址是沈海虹的表姐的公司的。她叫尉仪。
陈嫣一边在心中默念这个名字,一边把车——确切的说是一辆警车,停得离目的地远远的,尽量不引人注意。她穿过马路,又向前走了一段,进了尉仪供职的那家又小又挤的广告公司的办公楼里。
楼有两层高,是由北洋政府时期遗留的法式建筑改建而成的——增加了门与窗户的面积,打去了两堵承重墙,地上贴了光可鉴人的墨绿色瓷砖,墙上刷了雪白的乳胶漆,天花板不仅吊了顶还贴了石膏线,一盏盏日光灯嵌在向上凹的吊顶灯槽里犹如一只只鬼魅般的巨眼向下俯视着这方不盈尺的狭小空间。
“您来联系业务吗?”服务处的小姐问。
“不,”陈嫣回答,“我来找人。”
“哪一位?”
“尉仪。”
“尉仪小姐在二楼的……”服务小姐的话还未说完,陈嫣就听得身后一声大喊:“尉仪!”紧接着肩头挨了重重一击。
陈嫣诧异的回过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陌生的脸孔。
很显然,那人也愕然了,笑容在脸上凝固住了,愣了足有两秒钟才慌忙道歉:“对不起,我认错人了。你和她在后面看实在是太像了。”
“没关系。”陈嫣又回过头,听服务小姐把话说完。
楼梯是木制的,显然经过了加固,但走在上面总是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似乎还有“吱吱”的响声,但侧耳细听时又没有了。心理作用。陈嫣想,心理作用。说实话,陈嫣非常不愿意来这种旧楼,不仅时时刻刻都有倒塌的危险,而且传统上诸如闹鬼、分赃、凶杀一类的事情又特好在这里发生。陈嫣不怕鬼,更不怕犯罪,只是她觉得,在那些黑暗的角落中潜伏着比鬼更可怕的东西——她还清楚的记得她上大四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那是一个漆黑的下午,台风在化学市附近海域过境,导致整个化学市降下了罕见的特大暴雨。天空中阴霾密布,云头低垂。闪电自云层中迸出,几乎贯穿天地,之后便是摇山动地的雷声,然后又是如千军万马奔腾呼啸般的雨声;如此反复不息。
浑身透湿的班长推开教室的门,对里面唯一一个人说:“陈嫣,教授叫你去他办公室。”
“我知道了。”
于是,陈嫣穿过心理系大楼阴森而古怪的长长的走廊,向教授办公室走去。
那是一间独立的小办公室。陈嫣敲敲门,听到“请进”后推门进去,又随手带上门。教授背着手站在窗边,背对着门。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闪电,他一次又一次的变得惨白。
“您找我?”陈嫣问。
教授沉默不语,始终背对陈嫣。良久,才开了口。
“陈嫣同学,你相信世界上有鬼吗?”
“不相信。”
“那么,你喜欢心理学吗?”教授的声音相当严肃。
“是的。”
又是一道惨白的闪电,在没开灯的屋里格外令人心惊。
“……鬼的居所就在人的内心深处,心理学极力探索的地方。有几个人,就等于有几只鬼潜伏着……有两个人,就是有两只鬼……欲望,快感,意念,甚至是情绪都能引它们出来……鬼这种东西是无所不在的……”
手机响了起来。陈嫣走到僻静处,接了电话。是周涛打来的。
“喂,陈嫣,我是周涛。你找到尉仪了吗?”
“还没有,我刚到地方。怎么了?”
“找到沈海虹的遗书了。”
“真的还是伪造的?”
“送到技术科鉴定了,下午出结果。”
尉仪留着一头长发,大约垂到肩胛以下;戴着一副黑色粗框的小镜片近视镜;穿着一身绿色的格子纹衣服——外套和裤子,里面是一件刚买不久的白衬衣。陈嫣找到她时,她正坐在桌前分色。
“我就是尉仪。您是……”尉仪透过镜片好奇的打量着来客,揣测她的身份。
“我叫陈嫣,供职于化学市刑警大队。出了一点事,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尉仪紧张起来,表情变得十分复杂,局促不安的看了看周围,确定没有人听到后飞快的点了一下头,又略一迟疑,“不过,可以到阳台上去吗?”
阳台上非常脏,落满了灰尘,看样子平时几乎没有人来。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陈嫣问。
“呃……一开始在自己家里,八点半多去了海虹——就是我的表妹家,不大到十二点又回来了。”
“你在你表妹家的这段时间里,你们都在干什么?”
“随便聊一聊,还下了一会跳棋。”
“还有吗?”
“海虹还给我看了她的画。”
“聊的什么?”
“记不清了。”
“你为什么会去你表妹家?”
“她给我打电话,要我过去陪陪她,我就去了。”
“你昨天一整晚的行动有除你表妹之外的人能证明吗?”
“没有。警察小姐,您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吗?”
“今天凌晨有人在沈海虹家中发现了她的尸体,我们目前还不能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
梨花比来的时候少了,大部分落在了地上,少数则随风开始了旅程。
陈嫣依旧站在楼下的一辆车旁,没有事可干。远处,在远离救护车的地方有同事在向尉仪和那名中年管理员以及沈海虹的几位邻居提问;三号楼顶的天台上也有人在勘察。
陈嫣觉得自己的推理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怪圈——按沈海虹生前打来的那个电话而言,凶手应该是生人;但现场来看,却只有可能是熟人作案——或者,沈海虹的电话是打着玩的?陈嫣皱了皱眉头,没有动。
“在想什么?”身边有人问。陈嫣没有回头,她知道是周涛。
“……想来想去都觉得奇怪?”周涛问。
“是的。”
“我也是。刀上的指纹只有沈海虹一人的,其它的都被擦掉了。苏文毅他们认为是熟人作案。”
“那个电话有些别扭。”
“我在想,是不是沈海虹打着玩的?”
“报假案?”
“差不多,不过现在也是死无对证了。对了,你去找尉仪的时候,我们调查了一下她的亲属和朋友,发现在云台山市的熟人只有尉仪一个;如果是熟人作案,尉仪的嫌疑最大。不过,她的作案动机……几乎是没有。”
“但她昨天晚上来过沈海虹家,而且又没有不在场证明。”
“可没有证据也是白搭。”
两人沉默了许久。
“对了,周涛,”陈嫣忽然开了口,“听说过神经官能症吗?”
“强迫症?”
“狭义上讲,神经官能症又叫神经症,与强迫症是一回事;但从广义上讲,强迫症只是其中一种。相当一部分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出现幻视与幻听,通常表现为感觉有人跟踪自己,甚至想杀害自己,但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医学上称之为妄想症与迫害症。”
“你是说——”
“是的。我怀疑沈海虹患有严重的妄想症与迫害症,不仅严重的影响了她的生活,甚至已经连累了尉仪,于是她起了杀意。”
“可是我们搜遍全屋也没发现病历一类的东西,只有一些安眠药,但像沈海虹这样搞艺术创作的服用镇静剂或兴奋剂不足为奇。”
“很多人都回避心理医生,她很有可能不曾诊治过。”
“倒也是……啊,对了,我差点忘了,我去居委会了解情况,听说沈海虹常到老年活动室去玩。”
“玩什么?”
“和老年人下跳棋,听说还下得很好。”
跳棋!
(下)
陈嫣拿着一盒跳棋从老年活动室出来。刚才她在里边向几位老者了解了一下情况,又借了一副跳棋。
沈海虹在这里的人缘似乎很好,而且在被询问者的话语里并未流露出她有心理疾患的意思。但陈嫣并不着急,丝毫没有认为自己的结论被推翻——绝大部分心理疾病患者行为与正常人相差无几,通常都只是认为其性格不好或是有些怪癖,而这些在描述时又往往被忽略。
我需要试探一下尉仪,陈嫣想,她看来并不是特别沉着和无情的人,那么她对于昨天晚上的谋杀行动一定还心有余悸;按她说的,她最后与沈海虹下了几盘跳棋,这也是沈海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不会没有特别反映的。
尉仪倚在一辆车的车门上,仿佛是忧愁悲伤过度,哭不出来了一样,低着头默默无言。旁边有一名警察在安慰她。
“可以和我下一盘跳棋吗?”有声音随着风和梨花花瓣传了过来。
那名警察抬头看到陈嫣,又见了她的眼色,便离开了。尉仪看见她,愣了一会,才不连贯的答了句“可以”。
棋盘在汽车发动机盖上铺开,宛若中世纪欧洲的六芒星魔法阵。
“你先走。”陈嫣说。如果沈海虹棋艺真的很好,她一定会让着表姐的。
尉仪走了一步,陈嫣也按询问来的沈海虹的棋路走了一步……陈嫣看出尉仪越来越慌张——那是当然的,因为陈嫣的每一步都酷似已经死去的沈海虹……
“我——”尉仪似乎下决心终止这盘棋。
“有时候我会想,”陈嫣不经意的打断了她的话,语气有几分认真有几分漫不经心,“我永远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是否晋升,是否撤职都要到了‘今天’才会知道。但如果我下完这盘棋就死了,也就没必要想什么今天明天的了——想起来总是觉得很伤感,不是吗?”
尉仪不作声。
风又起了,吹得一树树的梨花韶华尽谢,这种观赏用的梨树是结不了果的,每年只有那么几天的花期,一时明朗起来,却又很快归于沉寂。
“我查了沈海虹的病历。”陈嫣说了谎,“最近几年她常去看心理医生;我又问了周围的人,听说她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生活也许不是那么快乐吧……请你不要难过,也许于她而言,死亡反倒是一种解脱……”
尉仪哭起来。
“自首吧,那样最重也不过是无期徒刑。”
陈嫣独自一人走在昏暗静寂的人行道上,她觉得有人在跟着自己——是的,是有人在跟着自己,这不是错觉,她可以肯定。自从她离开刑警队的院子后她就觉得有什么人一直在暗处注视着她,尤其是在过了绶安桥之后,她几乎无法忍受了。她快步向前走着,恐惧在心中渐渐的升了起来。她猛的停下并回过身去,看见一个人影倏的躲进了街侧的胡同。
“站住!”陈嫣叫着,立刻追了过去,但是那个人开枪了,子弹打在砖墙上溅起的碎屑崩到了她身上。当她再看时,那人已经不见了。她把弹头从墙上起了下来,是“五四”式手枪的。
她惊魂未定的回到家里,想要给队里打电话,但是想了想又算了——她想到了,那个凶手有可能认错人了。
第二天早上陈嫣一到办公室就给那个中年管理员打了电话。
“三号楼上有没有住着军人?”她问。
“我想想……啊,有,有,有一个,好象是个少尉吧。”
“干什么的?”
“好象是管什么仓库的。”
“枪械仓库?”
“对、对,没错。”
“他平时有没有什么暴力倾向?”
“没有。”
“你和他很熟?”
“一般。”
“你觉得他怎么样?”
“人挺好的,就是……”
“什么?”
“有点疑神疑鬼的。”
——完全明白了。
陈嫣谢过管理员,挂上了电话。此时恰好周涛进了办公室。
“给谁打电话呢?”他随口问。
“还记得昨天早上我在沈海虹家里遇到的枪击吗?”
“当然了,我昨晚还在想。怎么,得出什么结论了吗?”
“差不多。我认为那个枪手同沈海虹一样患有心理疾病,总是觉得有人要加害于他,于是他时时刻刻观察着外界。尉仪杀了沈海虹后转身的那一刹那被他捕捉到了,他认为这个人下一个要杀的就是自己,于是决定抢先杀了尉仪以保护自己。但是,他只认识尉仪的背影而没有看到她的脸。你应该能看出来,”陈嫣转过身,背对周涛,“我从后面看与尉仪非常相象,于是当我背对窗外时他开了枪。”
“……”
“我刚才打电话给沈海虹楼上的那个管理员,证实三号楼上确实住着一个符合条件的人,我建议先去监视他,或者进行搜查,找出证据。当然,我也不反对请他来这里坐坐。”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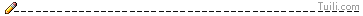
|
Es ist ein Schnee gefallen
Und es ist noch nit Zeit
Man wirft mich mit den Ballen
Der Weg ist mir verschneit.
Mein Haus hat keinen Giebel
Es ist mir worden alt
Zerbrochen sind die Riegel
Mein Stüblein ist mir kalt.
Ach Lieb, la dich''s erbarmen
Da ich so elend bin
Und schleu? mich in dein Arme!
So fahrt der Winter hin.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