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chzhch(行列式) zhchzhch(行列式)
|
|
|
1 楼:
天鹅记
|
05年08月15日17点58分 |
天鹅记
蓝蓝的轻纱接近无限透明,溶溶泄泄,似滟滟的波纹。小小的白鹅排成六乘四的方阵,在湖里盈盈漂动。
张石赶到剧院时《天鹅湖》第二幕刚开场。他静静冲到自己的座位,细心的妹妹早已备好观剧专用的望远镜放在两人之间。为了不出声影响别的观众,张石在按着望远镜的手心里划了三字:
“谢谢你。”
“不用谢。”素手微颤。
“你的手好像比平时暖一些。”张石举起望远镜,“好一群可爱的小鹅儿。可是,那为首的白天鹅——如此纤细的胳臂怎又如此稳健?如此沉着的步履怎又如此轻灵?如此妩媚的面容怎又如此幽怨?如此冷静的姿态怎又如此多情?呵,她是哪位舞者,还没到老得不能演白天鹅的年纪,竟能表现白天鹅的丰富内心?”
“今天是三巨星的告别演出,阵容百年一见。”妹妹一笔一划在他手心描着,“白天鹅——木思婉,”
“原来如此,她可是中国第一代英版的白天鹅呢。自国内有芭蕾舞以来,满眼尽是俄版天鹅。动作固然舒缓大方,若论脚背功夫、指尖传情,种种细节见其底蕴,则英版天鹅更胜一筹了。”
“嗯。饰黑天鹅的是舞团的台柱齐芙莉小姐。”
“怎么?自从1894年佩季帕与伊凡诺夫的版本上演,公认黑白天鹅由同一女演员扮演。”
“这个……可是戈尔斯基改编的版本里黑白天鹅就是由不同演员跳的呀。”
“不许狡辩,你明知道那个版本舞蹈贫乏是个笑话,何况是1920年的,不可能重排的。”张石略顿,“可叹佩季帕是芭蕾之父,世人敬仰百年,他的版本也高高供起,不敢问津了。”
“呵,又大发议论了。你可知今日白天鹅之娴静易得,黑天鹅之倜傥难求。寻常舞者多流于妖娆,试想黑天鹅若无高贵神采或更胜之,怎可与白天鹅媲美?则连王子的智力一并弄低了。说到这齐芙莉小姐享誉多年,在下最心仪……”
“当然当然,卿生也晚,她的32个fouettes前后十年无人能及。可是,快瞧,王子出场了,他的托举,就像擎起一支莲花一样不费力。他是谁?”
“还记得前苏联的‘托举之王’古雪夫吗?台上这位人称‘中国的古雪夫’——容可聆!”
容可聆!一晃十年,别来无恙?
张石的望远镜就像剧中王子的弓箭,台上身影流动忽疾忽徐,台下目光流动忽快忽慢,而思绪的飞速流动无人能羁,亦无人能见……
二十五,不,是二十六年前,那一年怎么会忘记呢?是张石和容可聆携手第一次去看芭蕾呵。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托举之王’古雪夫!云样的白纱裙中间,他那么沉稳而灿烂,像北极星……是《吉赛尔》里的阿尔伯特,还是《舞姬》里的索罗尔?阵形似曾相识——对了,就是王子,就是《天鹅湖》,不过跟今天的不一样,是1953年布尔梅斯杰尔的那个版本。——且不提张石发考据癖,当时容可聆怎么说?“我也会成为‘托举之王’。”注意,是“我也‘会’”而不是“我也‘要’”。与其说是斩钉截铁的信心,不如说是预见未来的宿命。“我也会成为‘托举之王’。”他这么坚决地说,仿佛叙述一个必然的事实,“我会成为‘中国的古雪夫’。”张石知道他既许愿,说到做到。那天是他五岁生日。张石五岁半。
下一次见到容可聆时,鲜红的西班牙式的绣金紧身衣让张石眼花缭乱。他还没被观众称为“中国的古雪夫”,但在团里已经有美名“中国的切凯季”了。20世纪“俄罗斯演出季”风靡欧洲的年代,切凯季虽非第一主角,但出类拔萃,德才兼备,斯特拉文斯基称他是“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良心”。二十岁的容可聆也是如此。张石特别欣赏他这个《唐吉珂德》里巴西里奥的造型,轻巧而不轻浮。身躯飞腾,双腿倒勾,悬在容可聆腰间而双手翻花做“鱼游春水”高难动作的,是他的令妹容可馨。十五年前她尚在襁褓,可曾听到乃兄的壮志?为何也立起足尖,踏上舞台?一举一动间,张石想到这也是绰号的来源——当初俄罗斯芭蕾舞团切凯季的夫人面貌酷肖其夫,那位鼎鼎大名的经理人谢•佳吉列夫叫她“穿裙子的切凯季”。容氏兄妹同貌,偏偏容可聆台下又不爱让她穿裙子,两人必定同样装饰,真是一对怪人。
张石神游之间,蓦然发现最精彩的一段群舞不知什么时候从眼前滑过去了。经典的阵形变换呢?白天鹅的独舞呢?王子的托举呢?只见白天鹅与王子在谢幕。
倒是妹妹一定看得认真,此刻已拉着张石的手大写评论。张石只辨出末一句是“你以为呢?”
“我以为他们跳得很……”张石一笔一画,“慢。”
笑而无声,张石却能感觉到她肩膀起伏。“是音乐的缘故吗?”他自己的手却也慢得几乎不动。
呵,亲爱的读者,谢谢您有充分的耐心读了这一千七百字。篇幅既长,假如字符的飞舞各有自己的速度和韵律,这些字也属慢步舞吧。将近两千字,就是说,差不多一个完整的短篇小说的量,还没有洒一滴血,郁闷和作者第一次看《天鹅湖》二幕云山雾罩不见高难技巧是一样的。然而看后面黑天鹅双人舞模仿白天鹅,还有结尾大规模群舞时才觉得前头的铺垫是必须的呀。请稍安勿躁,咱们这就来一小插曲,好比《天鹅湖》三幕的西班牙舞和匈牙利舞,不是卖弄花哨,却也有意义。
“为什么会跳得很慢?”张石摸一下额头。
“听说人家容可聆十年没碰过《天鹅湖》了嘛。”
“《天鹅湖》本是经典剧目。”
“白天鹅本是经典角色。”
“然而不是最经典的段落。”
“最经典的是哪一段?”
“你听说过?”
“我没看过?”
“国内已经十年没演过。”张石写“十”字特别用力。
“莫非就是你提到的f……?”
“fouettes挥鞭转,女演员一腿支撑自转,另一腿像鞭子抽打身体般不断挥动,由此可转过整个舞台。”
“啊,《唐吉珂德》结尾巴西里奥的旋转或《天鹅湖》开场小丑的旋转就是很难的呢。”
“那只是很难的技术,但黑天鹅,必须有红舞鞋般的魔力才能完成,代价是……”
“黑天鹅来了,快看!”
黑天鹅双翼翻飞,越跳越疾,仿佛在暴风雨般的音符中搏斗。她是在模仿高洁的白天鹅诱骗王子吗?竟有卡门的性格了!她肆意弯曲柔韧的腰身,卖弄敏捷的腿脚,轻若无骨,好像弹簧!笔者曾和张石讨论过近年排的几部芭蕾,每次都以义愤填膺告终。现代的女演员,除了木思婉等少数能演温柔单纯的白天鹅或睡美人,其余连带她们扮演的所谓朱丽叶或达吉雅娜,无不是轻狂的卡门!笔者三年前在英国的拉班动作与舞蹈中心遇齐芙莉小姐,与当年的容可馨似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以为非俗,不料今日。呵,你自己的告别演出,竟是这般不负责任吗?怪不得佩季帕1894年的版本要束之高阁了。
张石掷下望远镜:“今天不会有挥鞭转了。”
第三幕草草收场,甚至众人都没出来谢幕。
“难怪。其实卡尔萨文娜1906年版本就是没有挥鞭转的,也很流行。” 张石在妹妹手里写字安慰她。但最后两字自己都觉得很讽刺。
“刚才你明明说他们演英版的。”
“英版悲剧,俄版喜剧。最流行的瓦冈诺娃1933年版本就是俄版的。嗯,他们让你失望了,这很不好,也许会演搞笑的达瑞尔1929年的苏格兰版本作为赔罪吧。”
“索性让你过掉书袋的瘾,你最欣赏的是……”
“1995年,马修•伯恩的版本。”
第四幕居然是悲剧,而且是很动人的悲剧。王子与白天鹅的殉情摧人心肝。没有高难的托举和击腿反而让人专注于感情之力。
“终于等到了经典的结局。”
“可是究竟是什么打破了符咒,爱情,还是死亡?”
张石兄妹一边议论,一边看演员一个一个慢慢上台谢幕。四小天鹅,三大天鹅,群鹅走着之字形的队伍有一点《舞姬》的意思,仿佛无穷无尽,比第二幕还壮观。五分钟后,王后、宫女、小丑、魔王、黑天鹅、王子、白天鹅全部亮相。
今天是容可聆、木思婉和齐芙莉的告别演出。暴风雨般的掌声,为谁而作?
众人上台前那一分钟,妹妹的手似乎攥得特别紧,匆匆画了几字,抬头一看又舒手抹去,张石不清楚,只觉得与第三幕结束时画的字是一样的。
演员百般行礼之后,观众的第三次掌声才迎来了指挥。
群鹅布成方阵!
演员翼形分列!
灯光交叉照耀!
非此不足以扬资深指挥之威。黑衣黑袍,指挥尸体垂在幕前,脚灯把黑影映得与幕同高。
人声鼎沸。二人只好还是以文字交谈。
“我明白了。”张石一贯用语简洁。
“我呢,试着说说我明白的部分吧:舞台上的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垂下尸体的装置,无疑是和灯光电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有人在第四幕结束的时候迅速杀掉指挥,吊上滑轮。整个不超过十分钟。第四幕的音乐不是录音,也非无人指挥,虽然乐池黑暗,我们也看到指挥棒尖端的小红亮点,所以我说案件发生在第四幕结束后这十分钟里,演员们可来不及杀人,这就是台上诸位的不在场证明。”
“严格地讲,虽然这个版本,就像戈尔斯基的版本,与常见的不同……”
“对,第四幕时有一个角色是不在台上的,就是黑天鹅,但她身材小巧,又是女子,没办法把魁梧的指挥杀掉又吊挂。”
“果然是齐芙莉小姐的支持者。”张石补充,“同样的理由也可排除所有的天鹅。”
“你的意思是剧团的替补舞者。好了,你该告诉我你明白了什么,不妨从最经典的问题开始,谁是凶手呢?”
“呵,不是说那个,我的意思是,我明白了你在第三幕结束时写的什么字,而第四幕后又写了同样的字,怪不得你的手突然那样冷,因为那两字本就惊心动魄——杀气。”
“杀气……很大的杀气……”
“我能辨别第三幕的音乐比正常快了四分之一,你却能感觉到杀气。”张石写道,“这是我俩的不同。”
“嗯,当时我以为告别演出没有黑天鹅32个挥鞭转,齐芙莉可能痛不欲生;也可能观众大失望而生恨,很奇怪出事的不是她,也很奇怪没有挥鞭转。我感觉到的杀气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张石找到剧院老板,递上名片,说明他们对台上演员不在场证明的分析。摸黑回来时忽然后排的一位女观众轻若微风般对他耳语:“你可来了,这哪里是芭蕾舞剧《天鹅湖》,简直是音乐剧《歌剧魅影》呵。”
张石回头的一刹那,老板既知演员无辜,又见剧院里沸反盈天,不得不打开观众席的灯光,赫然见到后排手持望远镜的冰雕般的女士才是妹妹,而自己握着另一位的手,竟是一位精致得像瓷娃娃的少年。素未谋面,却似曾相识。
原来自己第二幕进场时坐得靠前了一排,人家的望远镜又和自己的一模一样所以错拿。张石沉吟片刻,说:“我明白了。”张石身为侦探,又好读传记,与此人神交久矣。
“幸会。”少年面若樱桃。
张石推推眼镜:“幸运儿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更幸运的是有一个出色的传记作家。”
妹妹取下面纱,颔首一笑。
片刻,d轻声说:“我们还是讨论一下案情如何?”
“演出中我们已经讨论很多了。”
“足下脑海中有那么多版本的《天鹅湖》……”
“眼前却是《歌剧魅影》。”张石与妹妹交流一下眼神,“关于小说的多彩案件暂且不提。音乐剧你看过么?被害者一个依旧是小说里的工匠,另一个是男高音,都被魅影的魔力套索绞杀。呵,魅影!现在你知道了,能把尸体吊在灯光装置中,并在适当时刻出现,一定是有非凡的凶手充分熟悉剧场构造。换言之,在我们排除了演员后,普通观众也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魅影……一个居高临下,可任意操控剧院的特殊观众。”
“年轻人,你知道我谈魅影的意图。”
“嗯。凶手杀指挥是有目的和原因的,虽然看似更可能的目标是黑天鹅齐芙莉。另外,当然也不是无差别杀人。”
“目的是什么?要么与演出无关,就像《歌剧魅影》里的工匠之死只因偶然窥破了魅影的秘密;要么与演出有关,魅影杀男高音正是为了取代他与心上人演对手戏。是早有盘算还是临时起意?”
“凶手又要全剧完成,又等不及指挥离开剧院,当然与演出有关。那么你要问了,演出有什么不对劲?海报早已公布,凶手如果不喜欢版本或阵容,就根本不会坐视上演。意外只有黑天鹅取消挥鞭转。转不转是演员自己的事,没有迁怒指挥的理。人家排练的版本也许就是不转。转不起来,你也说过,音乐太快……”
“太快也犯不着杀指挥是吧?”张石一瞥乐池,“你觉得快不快?”
少年低头玩弄表链。
“你能听出杀气,可见乐感不错,竟也听不出快了四分之一。”张石口气略柔,“凶手居然知道并非演员不想转,而是不能转,一切归咎于指挥太快。”
“所以凶手是精通乐理的人。”
“尤其精通《天鹅湖》!甚至胜过指挥……”
少年紧握双拳:“他指挥得更好!第四幕就是他指挥的!刚才我们推断案发时间,默认指挥没有人能替代,坚持到全剧终。其实第三幕后的黑暗中就被人绞死拖到帷幕间吊在灯绳上。反正乐队和观众只看到指挥棒上的小红亮点在打拍子。倒是真正的凶手堂堂正正指挥了《天鹅湖》的高潮,并享受观众的掌声!”
张石闭目凝神,掌声历历在耳。
“怪不得第三幕有杀气……”
“杀气?”张石重复着。
“魅影,你一直在提歌剧魅影,魅影替代了男高音,黑天鹅替代了白天鹅,凶手替代了指挥!我们刚才很可能忽略了一个人啊,第四幕台上真的是白天鹅吗?”
“白天鹅可能不在台上,但凶手一直在乐池里。谋杀和移尸是在幕间几分钟,我们说过,女子办不到。但王子和魔王确确实实跳了全幕。”
少年咬嘴唇:“白天鹅,黑天鹅?……黑天鹅没有取代白天鹅?”
“不是这样的形态,却是这样的故事。假的取代了真的,这个取代了那个。”张石翘起下巴,“再答不出要打手心哦。”
“小丑……唯一一个台下的男演员了。”
“他太小了。”——“啪!”
“难道魔王亲自出马?”
“魔王最高最壮,他换人早被发现了。”——“啪!”
“再怎么排除不可能的,也不是英俊的王子……”
张石佯怒:“不英俊怎么当凶手?——我是说,不英俊怎么当王子?”
少年直起身子:“不错!王子固然比指挥苗条许多,但膂力非同小可!容可聆,中国的托举之王!”
“托举之王在第四幕没有托举,黑天鹅在第三幕没有挥鞭转。这样的指挥岂可饶恕?”
少年面色如雪。艺术残缺不全,旁观者如张石尚以为暴殄天物,其罪当诛,则立志献身此道之容可聆何如?谋杀艺术者,杀之。这就是动机啊。
“好吧,完美的谋杀。我们理一下流程:第三幕后,王子容可聆见黑天鹅齐芙莉没有挥鞭转,认定是指挥之罪,按你的意思,是两重罪,他刚才不让她转,待会捣鬼不让我托举——问题一,旋转与音乐节奏有关,托举却无妨,既无两罪并罚,则罪不至死;凶手绞死指挥,接好绳索——问题二,既然装置电路与灯光相连,演出中间必开灯,中途尸体就会显现,那么他制造时间的假象就无用了;小丑演员接演王子——问题三,根本来不及换回衣服谢幕时第一个跑出来。三问并发,意下如何?”
张石赞道:“想得细,问得好!自己打手心吧。”
“阁下固然以眼力闻名,在下手持望远镜则亦未必不及呢。第四幕三人两两对手戏时,身材长短就有些不对劲。魔王比白天鹅高一头,比王子竟也高那么多。王子与白天鹅就应一般高才是。回想第二幕的确如此。可是那时白天鹅立了脚尖,也就是说,王子本身比白天鹅高。等到第四幕王子与白天鹅双人舞,两人还是一般高,细看竟都立了脚尖。腿脚功夫再好,芭蕾的规矩,男演员也是不立脚尖的。这位与白天鹅一般高,又会立脚尖,整整一幕都立得稳如磐石的假王子,就是黑天鹅齐芙莉了。”少年微微一笑,露出可爱的小虎牙。
“傻孩子,看那旋转就知道哪还有别人做得出呢。”
“黑天鹅没有替代白天鹅,竟然替代了王子……”少年的声音和双手都颤抖了,“这可能吗?”
“十年前的容可馨就可以跳他的全部角色。”张石平静地说,“齐小姐当然一样可为他舞蹈。”
“而他在为她杀人!”
“还记得我们在结尾讨论的命题么?”
“天鹅湖啊,打破符咒的只有爱情和死亡?!”少年悲愤地握拳,“世界上本不应该有这么多死亡。”
“世界上充满了死亡,正如世界上充满了爱情。”
少年握他的手。
张石看着他的眼睛:“大洋里巨轮穿梭,冰山游移,航线彼此交错,时间相互叠合,每一个点上都几乎无法逃脱碰撞。但人们不知道,很多时候它们被海风吹开一线之遥,只是因为一只蝴蝶偶然扇动翅膀。”
“你的眼睛太黑暗了。”少年抬头,“种因得果,你却一定归结为谋杀。比方说黑天鹅没有挥鞭转,错在指挥而罪不至死,即使指挥破坏的是他们的告别演出,即使齐芙莉是容可聆的爱人,即使他和你为有缺欠的舞蹈失望万分。生命总比艺术宝贵得多!”
“还有呢?”张石懒洋洋地抬起眼皮。
“还有,舞台上还有对手戏的演员,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王子和黑天鹅玩偷龙换凤的把戏。无论杀不杀人,戏都乱套了。”
“哦,残缺的艺术么?艺术并无一定之规,譬如这一剧之中,或悲或喜;一曲之中,或快或慢,自有不同的情感和价值。然而倘若你想来32个挥鞭转,这就不仅仅是心理学而是物理学的问题了。音乐快,转得就要快;转得快,公转的半径就要大。所以进程没到我就说她不会转了——那么快的音乐,要转就会飞出台去!”
少年惊呼:“指挥谋杀艺术,竟以谋杀生命相威胁!”
张石扣着他的双手:“你在第三幕感受到的杀气,不是有人要杀指挥,而正是指挥的心声——他要杀别人的心声。既然是告别演出,他们事先排练中当然是有挥鞭转的。指挥棒,就是红舞鞋,致命的旋转可在三千人的目击下无痕迹地把她推上死路!只是非常偶然地,黑天鹅错过了死路。而指挥自己在再次谋杀前被杀死。”
少年沉吟:“世界上充满了死亡……”
“即使齐芙莉不是容可聆的爱人,即使任何一个知道真相的人也不会无动于衷。有一种甚至远远超过爱情的力量……”张石望着舞台上白天鹅矗立如雕像,魔王躺在布景里静静地吸烟。
“正义感。”少年与张石相和。
“正义感……”似有回声。
一只洁白如天鹅翅膀的手向张石伸来。除了容可聆还会是谁呢?
“张石,你可来了。”
“十年没见了。”张石起立。
“十一年。”
“如今你又要飞走了?”
“是的,我们这些演员已有了不在场证明就可以走了。我会飞到山林水泽,远离人烟。”
“比翼双飞?”少年羞怯地问。
张石提醒少年:“你不是对计划感兴趣么?”
“没有人计划谋杀。”容可聆说,“假如你问的是排练计划,我们排的是悲剧版本。你可能注意到第二幕音乐和舞蹈较慢,比喜剧版本慢,这是爱情中死亡的影子。指挥憎恶这个版本。按他的速度,第三幕有许多技巧都不能做,第四幕也必须是喜剧了。”
“现在第四幕是悲剧,结尾就不是云开日明,那盏红色的大灯就不用打了,对不对?”少年说,“所以第三幕末挂好尸体的电路,不会在第四幕中接通。”
“是的。”容可聆冷冷地,“第三幕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只能尽自己的力演出最好的结果,告别艺术生涯。第三幕那样子,我们没脸谢幕,懂行的观众也不会鼓掌,所以那指挥临死得到的是冷场。第四幕我们奉献出全部本领,掌声呢,是演员应得的,给指挥的欢呼呢,是我应得的。这就足矣。”
“你的艺术本不是谋杀,而是舞蹈。可是观众仍然没有看到你的艺术。”少年替他惋惜。
“观众看到了齐芙莉小姐的艺术。我俩本不分彼此。”容可聆细长的眼睛闪过一抹亮光,“何况,观众听到了我的艺术。”
“你的指挥艺术……”
“已经深藏太久了。”
张石出神半天,忽然发问:“容可聆,我们是十一年没见了。”
“十一年。”
“本应是十年的。”
“本应是十年的。”
“国内十年没排《天鹅湖》了。”
“是的。”
“你十年没动《天鹅湖》了。”
“是的。”
“国内最后一次就是你演的。”
“演出后我在英国待了十年。”
“十年前我们本应见一面。”
“十年前我邀请了你。”
“可是我有事错过了。”
“我等了你十一年。”
“那次我错过了什么?”
“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
“很抱歉错过了那次令妹容可馨的告别演出。”
“所以你再也没看过挥鞭转。”
张石再不多言,摘下眼镜逼视其双眸。
容可聆一字一字地说:“那次她从舞台飞了出去。音乐快了三分之一。”
“啊!”少年掩面。
“她硬要转,因为那是她的告别演出。”
“而我错过了她的演出,”张石上前一步,“我竟然非常偶然地错过了。”
“你错过了,或者不如说,她错过了你,张石,”容可聆几乎把张石的肩膀捏碎,“警方认定是意外事故。剧团老板也信了。指挥留用。”
“于是你不再动《天鹅湖》。”
“木思婉性格温柔如白天鹅,在她的安慰下我竟能遇见齐芙莉,一切都是偶然,一切偶然都是宿命!”
“死亡,爱情,符咒……”少年默念。
“是的,幻影遮住了仇人。我当上剧团老板的第一件事就是排练告别演出,然后与我的两只天鹅偕老。结果……发生了今天的一幕,意外地,音乐变快了。”
“天衣无缝,全是意外。”少年叹道。
“十年间,我张石偶然的缺席,你与齐芙莉偶然的相遇,令妹一闪念之间的旋转和齐芙莉一闪念之间的不转。世界上充满了死亡,人们与之匆匆擦肩而过或是当面相逢。”
“嗳,你的眼睛太黑暗了。”容可聆天鹅般的超脱神情,“你该多跟年轻人在一起。我要飞走了,带走我的天鹅,不在湖面留下一个倒影。”
“比翼齐飞……白天鹅与黑天鹅。” 少年沉思。
“我的天鹅。”容可聆高傲地昂首,强壮的臂膀勾出长长的曲线。这让少年想起书上说自然界的天鹅并不是舞台上少女般优美,愤怒的天鹅甚至可以攻击大船。
“童话里,天鹅纯净无暇。”张石对妹妹说。
“是的,天鹅骑士。”
少年念着他的名字:“再见,再见,容可聆……”
张石用德语念着他的名字:“再见,再见,罗恩格林!”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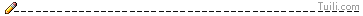
|
FROM MATH’S AID AND ART
NEVER WILL FAME DEPART!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