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知我哀(秦我) 莫知我哀(秦我)
|
|
|
1 楼:
长眠不醒
|
07年02月14日19点56分 |
长眠不醒
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当几个警察冲进房间的时候,他们的手指和神色都像琴弦一样紧绷,枪里的子弹在弹夹里不安地乒乓乱响。
在冲进这个房间之前,几个警察的脚尖不安地向后动了动。
房间里充满了酒味。女孩七扭八歪地瘫在床中央,面色潮红。随着呼吸,黑色的微蜷的头发像寄生虫一样蠕动在她的脸上。她的手里握着一只空酒瓶,一点点液体在里面中了弹似的爬动。她的另一只手交替着握拳和放松;她发出轻微的鼾声。而那床,看起来就像是垃圾场的地面肮脏般。
子弹不安的乒乓声一下子停息了。警察们面面相觑。
“‘极其危险的职业杀手’。”一个警察没好气地说,“酒鬼职业杀手!我看上头是疯了。”
女孩在睡梦里嘟哝了几声。屋里陡然充满了轻松的气氛。一个警察笑着呼喊了她几声。她翻了个身,再转过来的时候,手里已经多了两支手枪。酒瓶掉到了床上。黑色的枪身像是要埋在她黑色的长发里。空气像一块玻璃被硬生生掰断,她呼吸急促。
“都给我出去!”她的声音嘶哑,像一只兀鹰在坟地上盘旋。没有人动。
“听见没有,都给我出去,谁叫你们进来的!”她声嘶力竭,床上的酒瓶不安地震动,“都给我滚,你们干吗管我!像以前所有人一样,滚出去!”
潮水在缓慢地向门边退回。这时,仿佛从时空的另一端传来一声低语:“你们这群笨蛋,把房间号搞错了!是隔壁!”于是门在疑惑中被关上了,遥远的声音在低声争论:“她有枪,她不是那个杀手又是谁?”
门关上的一瞬间,她也重重地摔倒在床上,眼皮耷拉下来。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后他们再次闯入时,却惊讶地发现她没有逃,依然人事不省地陷在床上,手里握着两把手枪——手枪?其中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接近她,仔细端详着手枪。那是相当逼真的玩具手枪。他笑出了声。同情地吸着房间里带有酒的腐臭味的空气,他带上了门。
眼睛一般黑的街道上,黄色的灯光像是廉价奶油。
几个时髦的年轻男女正嬉笑着互相追逐。前面女孩们的手臂挽在一起,后面男孩的笑骂声在空旷的街道上跳起无数回音。汽车的灯光助兴般划过,他们觉得快活之极:像是处在舞台中央,整个世界都在随他们而扭动。
一只手在他们的背后伸了出来。这只干枯的手不合时宜。老乞丐的眼睛已经是不见天日的坟墓,白沫随着刺耳的啊啊声从嘴角淌落。她是他们舞台背景上不和谐的黑色污点。
他们小步地奔跑着,尖声笑着。他们的快活与她无关。相反,她手里恶心的碗已经碰到了他们时髦的外衣。他们跑得更快了;她跟不上。一辆驶过的汽车把车灯打得像把刺刀。突然间她咧嘴笑了,向着汽车一瘸一拐冲过去,把碗伸向汽车的窗口。嘴角流着白沫。
汽车司机狠狠一拐弯,避开了她,嘴里骂着脏话。她嘻嘻地笑。
一个男人从昏暗的路灯下走开。那尖笑声刺刀似的戳在他的耳膜里。
我觉得头痛欲裂,那肯定是宿醉的后果。电话铃响了起来,没完没了。我瞪着它,像看一个陌生人。电话顽强地响了一分钟。我克制住拿枪打碎它的冲动,接起电话。
“是江先生吗?”话筒一边的声音陌生有礼。
“不。”我疲倦地回答。
“那么,我找江离。我想这个就是他的联系电话吧?”
“我就是。”
电话那边半晌沉默。我烦躁起来,觉得自己的头发开始啃咬自己。
“没想到江离是位女士。”电话那边的声音慢条斯理,像是咀嚼着什么一般。
“少跟老鼠一样咬文嚼字。”头发已经开始啃我了。
“我知道,我不该相信那种街头小广告。那些所谓私家侦探,都是些没本事找工作就来糊弄人的毛头小子。但是我有位朋友向我推荐你。原来他那种看好戏的神情是因为你是位女士。”电话那头的男声若有所思,“那么,我想委托你监视我的妻子。我可以付定金。”
“可以。”
“我没有打扰你的日程吧?我希望你今天就开始。”
“我像守墓地的人一样无事可做。”我瞥到了地上的空酒瓶。我应该少喝点酒。
“很爽快。那么,有关的资料以及定金请你上这里来取。我在这里等你。”
我潦草地记下了那个偏僻的地址。电话挂断了,我发了一会呆。每次发呆我都像是沉入了两百米深的海底,每次被自己拉出来的时候都像是经历了一场绞刑。我努力想些什么,但是什么也没想到。随便扒拉了一下头发,燥热已经退去,头发看起来海藻似的温顺。我拎起空酒瓶,垃圾桶里一阵响亮的骚动。
“你们听说了没?有名的老板找到了他妈,找到的时候他妈正在要饭!”
“老乞婆运气的很呐。他儿子还在报纸上哭着保证说,一定要把大笔钱放到他母亲的名下,说什么他欠她的太多。”
“这年头,什么事都会有。说不准哪天就有谁要我继承千万遗产了。”
餐馆的另一边爆发出一阵大笑。粗野的男人拍着女人的肩膀说做梦吧你。女人嘻嘻傻笑。我瞥了一眼那个浑浊的角落。我已读过当天的晚报。记者以感人肺腑的文字讲述了一个富豪、慈善家在街上偶遇失踪多年,现在沦为乞丐的母亲。他认出了她脸上的痣。他当街抱住母亲哭了起来,而老乞丐在他怀里嘻嘻傻笑。他牵起母亲肮脏的手把她带回自己富丽堂皇的家。而他的妻子也温暖地欢迎了她。
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人间。
而梁柯,这个处在焦点的富豪兼慈善家,却打来电话,要我监视他的妻子吴雪。
他解释说,他了解他的妻子。记者面前她很会做戏。但他能察觉到她的嫌恶和憎恨。
他说,他觉得母亲在危险中。他希望我监视自己的妻子,直到他认为危险的时期过去。
而我,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个该死的工作。我又能选择什么呢?我没有什么该干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干的事情。我的口袋里是不菲的定金。从最初到现在,我本来就没有别的选择。
我看着吴雪把牛奶端给新来的丈母娘,看着老人喝完,关灯,睡下。那只乞讨用的破碗摆在床头柜上。吴雪曾试图把它塞进抽屉,然而老人一旦发现碗不见了,就会眼含泪水,口冒白沫地四处寻找,把口水滴到吴雪新买的地毯上。于是那只碗就一直在那里了。
我看着吴雪来到厨房,用优雅而雪白的手指若即若离地扶着高脚杯,剔透的红酒如同流动的宝石。她用几个手指端着酒回到自己的房间,罩着耳机,在豪华的床上边呷着酒,边阅读一本侦探小说。她的丈夫今晚不会回来。我仿佛看到她朝摄像机的镜头笑了一下,然而那笑容一闪即逝。此时我正坐在离梁家不近不远的树林里,眼前是梁柯提供的笔记本电脑,活动着的是摄像头扔过来的图像。
有富豪做主顾就是好,能把你从原始社会升级到第二次科技革命。
但我的头又开始疼痛。我喜欢汽车,因为它像一个单人牢房。然而在一个人需要新鲜空气的时候把她关在车里,为了隐藏笔记本电脑的亮光而紧闭着窗,这并不是件令人喜欢的事。
头痛像拧螺丝一样拧着我的脑袋,屏幕不安地晃动。我是什么,只是一颗脆弱的钉子,脚可以踩弯我,钳子可以扭折我。我什么也不是。我可以被任何东西打倒。眼前的图像有些模糊起来。恍惚之间我听到了什么声音,从远处仿佛传来一声叹息。又一声。这叹息像是整个宇宙喊出来的。
又过了很久,我被刺耳的警笛声吵醒。手机里导弹般轰击耳膜的是梁柯迫切的声音。
“我母亲出车祸了!快告诉我,那时候我妻子在干吗?”
一滩肉酱糊在地面上,白森森的骨片凝固在血泊里,凝固在她身上破旧毛衣的缝隙里。只有她的脑袋是完好的,脸上的皱纹扭曲成一个迷宫,嘴角的白沫换成了一缕暗红的血。那缕血像是大地震后地面巨大的伤口。
她横躺在路的右半侧,一辆轮胎沾满鲜血的摩托车夸张地停在路边。一群警员正围着它仓鼠似的忙碌。我看着那辆摩托车。除了它的轮胎和车体沾满了鲜血,它是一辆非常正常、挑不出任何毛病的好摩托,高级摩托。用这样的摩托去轧人一定让人感到快意。梁柯正在远处悲伤地冲妻子大叫:“你怎么可以不锁落地窗,让她从房间里跑出去?难道你不知道她晚上毛病发作的时候还……还会出去乞讨,而且会朝汽车冲过去吗?”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了,“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对……对不起。”吴雪的声音像蚊子叫,“我没想那么多……对不起。”
闪光灯贪婪地起伏。记者们狼一样兴奋的眼神炙热地烘烤着空气。
然而,他们都是无辜的。我冷冷地看着这场闹剧。正是我手里的录像,证明了吴雪整晚都窝在自己的房间里。而梁柯的朋友们,异口同声地证明了梁柯的不在场。
只是某个聪明而愚蠢的司机为了逃脱无止境的医药费而去二次碾压。这里地处偏僻,是飙车的理想地点。然而那个莽撞的人完事以后,却不知道怎么处理他的摩托车,于是便把它甩在了路旁。而自己——走回去,跑回去,抑或滚回去——都随他便了。
最主要的事是,这里已没我的事了。梁柯所害怕的后果已经发生。虽然方式不同——我邪恶地想,这不同的方式似乎让他挺失望的。但这与我无关。我将回到自己的垃圾场——
让思维凝固的是一辆停在路旁的车,几乎挨近草丛。离尸体近十米远。我盯着它。我抽出手电筒蹲下身,在沙石满地的地面上看到几条平滑的车痕。那不是急刹车的痕迹。我直起腰打量着那辆车。前盖、挡风玻璃、保险杠、车灯、车轮,完好如新。
我拉住刚好经过的一个警察:“请去查一下这辆车的刹车痕迹。”
他脸上的青春痘惊讶地动了一下:“查它干什么?那是我们局长的车。这儿的事情就是他发现的。”
“这是半夜。他在干什么?”我并没掩饰自己的怀疑。
小警察吃吃地笑了:“也许是夜生活归来。你管他呢。”他作势离开,却突然噤声。他身后的男人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小警察像干草堆似的萎缩下去,无声地蠕动着嘴唇溜开。
“也许他不想当警察了,局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枯而没有起伏,“而如果我想继续当记者的话,我就最好问清楚,您为什么三更半夜出去兜风。”
“我想我应该有上夜班的权利。”面前的男人冷冷地回敬。我没有做声,点了点头,转身走向现场。他没有跟过来。我大踏步跨过警戒线,掀开白布。我试图不去看老人的头。
老人确实是一滩肉酱了。除了头部以外的身体几乎全部被碾压过,大部分地方,我看着尸体旁凌乱的摩托车血印想,被碾压过不止一次。凶手像锯木头一样把她来回锯了个遍。我再一次端详着凌乱的摩托车血印,却没有发现自己想要的其它痕迹。被礼貌地请出警戒线后,我站在那里发呆,面对一片没有底的空白。
“江小姐……”梁柯的声音。
不知什么时候人都已经散了。尸体也被抬走。吴雪也不见了。
“江小姐。”声音更近了,我转过头,看见梁柯的眼神,“我不相信那是单纯的车祸。这里面一定有阴谋,把我们都瞒过去了。”
“她不在现场。”我疲倦地说。
“我知道,但她可能知道我请了你,所以反而利用你做了不在场证明。”吴雪那一闪即逝的笑掠过眼前,然而只是一瞬间。“所以,我想继续请你调查。这回,是请你找出她杀害了我母亲的证据。”我张了张嘴,他挥手打断了我,“你别问我为什么不去找警察。我会去的。但是他们是明,你是暗。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接受你的委托?”
他怔了一下,随即不怀好意地笑了:“要多少钱,你说吧。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凝视着他,他的眼睛里是鄙夷的神色。我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笑,我想自己一定笑得像一只苍蝇:“既然如此,我接受了。”
“小姐,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我?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咖啡厅里,烟灰从吴雪的指间掉落,摔个粉碎,“你是记者,对吗?”
“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我盯视着烟灰的残骸。
“我可不相信这是什么善意的提醒。何况,”她短促地一笑,“你过时了。”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你的卧室里有摄像头?”我问。
“我亲爱的老公,他做得太明显了。他的表现让我明白,他知道我在卧室里的举动。我不是笨蛋。他怀疑我有外遇。但是,”她波光闪烁的眼睛浮动了一下,“我问心无愧。记者小姐,我得说,他是太爱我,害怕失去我,所以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我原谅他了。”
我疲倦地把头向后一仰:“咱们别再在这儿扯淡了吧,如果你也这样认为的话。”
她的大眼睛一闪:“你又想说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你往他母亲的牛奶里放了什么。”
面前的身体猛然僵直了。“你都知道什么?”她轻声地问。
“你会喜欢我们的计谋的。是我故意让你丈夫做出明显的样子,让你知道你的卧室里有摄像头。再让他表现出怀疑你有外遇的样子。如我们所想,你开始集中精力对付卧室里的那只摄像头,却没发现别的地方有更隐蔽的眼珠子。这可能挺让你发火的。然后我又想,你为什么不和你的丈夫哭闹撒娇,或者偷偷拆掉,却宁可放着卧室里的摄像头不管。这一切可以让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浮想联翩。对我来说,你是在制造你的不在场证明。”我冲她友好地一笑,“我在录像里,看见你往她的牛奶里加上了什么。现在你可以告诉我那是什么了吗?”
吴雪紧闭着嘴唇,那形状让我想起精致而冷酷的手术刀。“安眠药而已。”她干涩地说。
“安眠药而已!”我端过她面前的红酒,“如果是安眠药,她就不会从落地窗往黄泉走了。是兴奋剂一类的玩意。你暗示她可以从落地窗出去。所以她走出去了,拿着乞讨的碗。她是个惹人厌的老乞婆,专门往汽车前面钻。而你,在床上喝喝红酒,等着她被某个飙车的人撞死。几率很小,不过,总有一次会成功的。”我透过红酒看着她血红色的脸,“她会被碾死,就像现在一样。但是,摄像机拍到了你下药的瞬间,法医会在她的身体里检验出兴奋剂的痕迹,从而推断她什么时候被下了药。”
她的脸色却不那么紧绷:“她确实是被碾死的吧?”
“为什么不是?”我反问。一刹那的寂静,只有香烟灰的发抖声。
突然她大笑起来。
“亲爱的小姐,”她甚至笑出了眼泪,“如果我告诉你,你大错特错了,你怎么办?”
我没做声。错了又怎么样?我本来就与此无关。我又不是冤鬼路上的老乞丐。
“我知道你的计谋,你逼迫我自己承认,充当最后的证据。问题在于,你全错了。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你错了,但是我不能信任你。可是,”她若有所思,“你所说的录像也是一件糟糕的事。你喜欢钱吗?”她倾身向我微笑。她微笑的样子非常迷人。
“没有人不喜欢钱。”我回答。
“我给你钱,现金。你销毁那些录像。然后,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大错特错。”
“我猜你不知道我曾读过化学系。” 她从口袋里掏出瓶子,近乎自恋地看着它,等着我的反应。
“没必要知道。”意识到我得说一句她才会继续说,我不得已回应了一句。
“现在你就会知道这有必要了。”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子,“我很高兴我们现在不是在那些该死的眼珠子下面。这是DMN,学名二甲基亚硝胺。它是一种化学致癌物,可溶于水,毒性极强,只会对肝脏造成损伤,而且不会在尸体中留下任何痕迹。所以,亲爱的小姐,从尸体里检验出它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使用高性能液体色谱法分析DNA,但我相信这里的法医没有那么大想象力。”
“你想伪装成癌症。”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它。
“正确,又不正确。DMN用量大的时候,会使患者立即死亡,看起来就像肝病发作一样。对于一个不看病的老乞丐来说,那是不稀奇的。”她短促一笑,“你认为我会喜欢给她付医药费吗?”
“你保留了摄像头,不是想制造不在场证明,而是因为你确实有外遇,而你想让梁柯放下疑心。那么,杀死你丈夫母亲的动机,应该是你丈夫在报纸上信誓旦旦承诺要放在他母亲名下的财产。”
“你很聪明。”
“谢谢夸奖。”我冷冷地看着她。
“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我。” 她依旧微笑着,“事实证明,她必定要死,即使没死在DMN下,也还是死在了车轮底下。从一开始她就是个错误。现在,江离,记得我们的交易。如果你毁约,希望你料得到后果。”她的微笑迷人极了,在昏暗的灯光下如同猫头鹰的眼睛。
“没有人不喜欢钱。”我重复了一遍,转身走下黑暗的楼梯。
没有人不喜欢钱。
我回到破旧而昏暗的公寓,穿过一扇扇门牌破碎的门,打开我没有门牌的房间。各种臭味的混合味在房间里快活地翻滚。我把皮箱扔到床上,拨开纽扣,一叠叠钱像石头一样滚落在我的床上,艰难地滚了一下,就再没有声息,冷淡得像一颗颗砍下的透露。
我没有开灯,钱的味道其实就是细菌的气味,每一双手的汗臭味,验钞机里冰冷的电离味,每一颗脑袋里贪婪、冷酷和自私的气味,像幽灵一样在我的房间里打转,也在每一个最道貌岸然的地方,和每一位贞洁清白的女人亲密地跳着交谊舞。
那个从没有人关心的老乞丐,也许在她痴呆的大脑里,还有一丝儿子的影子。
她幸运地得到了儿子的温暖。而她的儿媳为了钱,决定杀死她丈夫的母亲。
吴雪的眼睛像红酒中的宝石一样闪亮。
而我现在,和钱同床共枕。这是件多么美妙的事啊,我突然觉得暴躁起来。
你毁了我,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恶狠狠地咕哝着。然后我便和满床的钱一起沉入空白的梦乡。
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去,房间里的空气污浊着我,使我不知日夜。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真正醒来的。反正当我打开电视,便在晚间新闻中看见了吴雪宝石一样闪亮的眼睛。
著名富豪、慈善家梁柯的妻子吴雪已被逮捕,涉嫌下毒谋杀梁柯的母亲,王兰。据说是一份法医鉴定书显示,王兰在被汽车碾压之前,就已经中毒死亡。而当天梁柯整天整夜不在家,只有吴雪和王兰共处。当吴雪被叫去询问的时候,她显得十分惊愕而慌张,在强大的心理攻势前很快承认了罪行。而因为导致王兰死亡的是吴雪,因此警方停止了对碾压事故的侦察。而且,摩托车上没有撞击的痕迹,也印证了王兰被碾压前就已经死亡的说法。
记者没有忘记复述一遍梁柯感人的寻母故事。王兰就是那个痴呆的老乞丐。
我记得,原先警方已经逮捕了摩托车的主人,然而那个人死活不承认是自己压死了王兰,还喊叫说,他去方便,把车没熄火停在路旁,回来就没有了。有可能是谁把它骑走,又压死了老人。
我坐在床上,思考了一会儿。
一支枪孤零零地顶在了我的脑后。一个陌生的男声在脑后响起:“别动。”
我的手停住了。枕头下有两支枪,我的反应又迟了一拍。
那个声音带着嘲弄:“也许你有枪。但是小姐,你太慢了。为什么不回头看看我呢?你的生命就要结束了。而我很擅长给将死的人最后的礼物。”
我回过头去,看见一张英俊的脸:“我猜是倒霉的吴雪叫你来送的礼物。”
他弯起嘴唇:“是啊,不过,她也慢了一拍。看来你还是让她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低低地笑了:“既然如此,你还有什么必要来杀我呢?她已经必死无疑。”
“小姐,我收了她的钱,我就得对得起那堆钞票。”他漫不经心地说。
“那么你现在的目的也就是钱了。那么,我想你也愿意对得起我的钱。如果你愿意放过我,床上的这些钱就都是你的了。”我用手一指。
他把头向后一仰,一阵肆意的笑声在整个房间里撞击出无数回声:“小姐,你真是傻得可爱!你该比我更清楚你的对手,她难道会让你死后这些钱留在这里?不,亲爱的,你死以后,这些钱就都是我的了。这是我的雇主给我的另一半报酬。”
“你拿不到的。”我举起枪,一声闷响,我听到他的痛呼,我在他的枪落地之前将它捉在手中,“你是个菜鸟。连我都知道,熟练的职业杀手不会把枪悬空地顶在目标的后脑勺上。那样就像空手握了一条泥鳅一样容易让目标滑脱。你的语气显示你过于骄傲。而且,真正的杀手是不会冒着被目标听到而做出防备的危险,把锁着的门给撬开。”我看了一眼被他撬开的门,“而我,我当然早就知道,美丽的吴雪会跟踪我到这里,然后雇人来杀我;我当然知道她不会叫杀手把钱带回去,而是给杀手做报酬。你嘲笑我的时候,我拿到了枪。”我注视着他痛苦地握着自己的手臂,扔给他一卷绷带,“把手包好,没有人喜欢血滴在自己的房间里。你应该庆幸我没打断你的骨头。”
他没有动,嘴唇紧闭。
“你是想让我给你包扎伤口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粗糙得像坟墓上的泥土。
“你这样会引来邻居的。”他终于开口。
“在这里你可以做任何事,开枪,拿酒瓶砸别人的脑袋,虐待或者谋杀妻子,没有任何人会来阻止你。你可以走了。再不走的话,就不会只是手臂了。”谈到这里的事使我烦心。我想让他尽快离开。
他打开门。
“还有,”我叫住了他,他回头,“把你这张漂亮的脸用在别的地方,只是别用来做给死人的安慰。这让我恶心。”
门无言地关上了。我浑身酸痛,感到自己就是一只被人捏握在手中的大白鼠。我很想再睡一觉,睡到世界末日,睡到等我走出去整个世界只剩一块浑浊的地壳为止。但我站起身,刻意避开那些血迹,把自己陷入了走廊中无穷的黑暗之中。
“你知道吗,一个装着钱的信封被放到了局里,还有一个要求说,用这些钱做一个DNA鉴定。”烟雾缭绕的小饭馆里,隔着一堵飘忽的雾墙,我听见对桌的一个人对同伴迫不及待地说。
“到哪里都有烧钱的人。”另一边传来含糊不清的抱怨声,似乎对方正在起劲地咀嚼着什么,“那么,是什么DNA鉴定?”
“那个慈善家梁柯,听说过吗?”传来一声模糊的应答,“那你肯定也知道他最近刚找到在当乞丐的妈妈的事了。这封信就要求说,做一下梁柯和那个——是叫王兰吧——的DNA亲子鉴定。”
“我不认为随便认一个老妈对他有好处。”另一个人终于吞下了食物,清晰地讽刺道。
“但是——你们知道吗——事实就是这样!局里的法医因为好奇——当然不是因为那钱——给他们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是这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那帮记者已经爆炸了,估计今晚的头条少不了。”消息的传播动者显得激动不已,就像自己要上报纸了一样。
这可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我倒没有料到会在这里提早听到消息。
那边又换了话题,开始讨论局长的儿子曾因偷窃入狱,谈论最近上头对刑警队特别关注而严厉。而对我来说,这已经够了。
我看见局长下车,关车门,锁车,掏出钥匙。他儿子的车已经停在车库里,像一具尸体。他走过拐角的时候,正好经过我的身边。而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四肢已经不能够动弹,而我在俯视着他。
“你的法医已经告诉了我一切。”我直视他的眼睛,“而且,想必你已经知道了梁柯冒认母亲的阴谋暴露的事情。”这是我在昨晚的报纸上看到的。几位记者同时收到一封匿名电子邮件,他们打开附件中的音频文件,却听见了梁柯与什么人交谈时的声音。那个声音承认说,自己冒认母亲,是为了引诱他的妻子谋杀“母亲”,然后他就可以借机离婚,使这桩离婚不损害反而会提升自己的名誉,而且也可以向法院申请不分给吴雪财产。他说,他知道吴雪会去谋杀,因为吴雪要的就是他的钱。所以他故意不停地在报纸上说,要把大笔钱放到他母亲的名下。
消息用最耸动的标题和最痛心的文字,如同当初讲述那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般,发在报纸的头条。只是我注意到,音频文件中的另外一个声音被抹去了。
而当我轻而易举地查出那名法医的住址之后,我在昏暗的楼道里从他的背后悄悄逼近他,勒住他的脖子,用手枪顶住他的腰,逼迫他吐露了他的秘密。王兰的尸检报告是假的,他并没有验出什么,然而局长要求他这么写,并承诺会给他提升。这对他是无法拒绝的诱惑。
我击昏了他,看着他像沥青一样瘫软在墙角的垃圾中。
现在,轮到我们的局长了。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那对眼睛,和吴雪的眼睛在黑暗中的闪烁一模一样。
“当初你和梁柯交易的时候,他并没有料到你会来这么一手。他很明白,这份交易之后你和他知道。我很惊讶,让他身败名裂,这样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当然,如果没有人相信他的说辞的话,他的这份告白确实会让整个‘儿媳’毒死丈母娘的案件更加真实。可是现在……”我掏出手枪逼近他的额心。我听到子弹在弹匣里蠢蠢欲动的声音,对这种声音我简直是厌恶之极。
可是我还是得用我干枯的喉咙说:“你让他身败名裂,他恨透了你。所以,他请我来杀死你。我不是记者,现在你该明白了。”手枪上的消音器冗重得像背了个枕头,可它不是个坏东西。
“听我说,小姐。”他终于试图说什么,“我没有……”
“对我辩解又有什么用呢?”我嘲讽地笑了,“不过,你还有一个选择。”他直直地盯着我,“雇佣我去杀掉梁柯。反正,不是你死,就是他亡。我给你两分钟时间。”
两分钟之后,我开着梁柯借给我的车离开。而惊魂未定的局长并不知道我带走了什么。
当警察误冲进我的房间时,我正好喝醉了酒,在永远是空白的梦境里找不到出口。房间里充满了酒味。我七扭八歪地瘫在床中央,手里握着一只空酒瓶。
“‘极其危险的职业杀手’。”一个警察没好气地说,“酒鬼职业杀手!我看上头是疯了。”
我听到梦里的远处有乒乓作响的打斗声,接着,所有的白色都疯狂地向我扑过来。我的手胡乱甩动,碰到了冰凉的手枪。但它是安全的,相反,每一具移动着的温暖的肉体才是最危险的事物。我一把抓住它们。我不知道自己对白色的侵入者吼了些什么,总之潮水在慢慢退去。门关上了。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从白色敌人的包裹中清醒了过来。我隐约觉察到我在别人的面前,亮了枪。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忘记了进入我房间的是些谁,虽然我隐约有些记忆。不管如何,我不喜欢坐牢。
我把仿真的玩具枪拿出来,把真的枪藏好。
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后他们再次闯入时,却惊讶地发现我没有逃,依然人事不省地陷在床上,手里握着两把手枪——手枪?其中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接近,仔细端详着手枪。那是相当逼真的玩具手枪。他笑出了声。同情地吸着房间里带有酒的腐臭味的空气,他带上了门。
我是在报纸上看到警察局长的儿子二次碾压,蓄意杀人被逮捕的消息的。新的法医报告鉴定老人的死因是车祸。局长引咎辞职。一个神秘的电话把警察们带到一幢破旧公寓中的一个房间,那里藏着局长儿子车上被撞坏的保险杠。法医验出了老人衣服上的纤维和局长儿子的指纹。
梁柯在认母骗局后被千夫所指,一蹶不振,新近被检查出患上肝癌。
吴雪疑精神错乱,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
我一个人走上公寓的楼顶。只有一个人死了,一个谁也不会在意的人,一个被当作工具的人。我曾看见她在黑暗的街道里追着时髦的年轻男女,手里伸出破旧的碗,嘴角流出白沫。我也曾看见她白森森的骨片,暗红色的血泊和迷宫般扭曲的脸。而现在,我什么也看不见。
一个人死了,其余的人都疯了,而且终将死去。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从看到老人的尸体起,我就确信,她是被一辆汽车撞死的。二次碾压,以及沾满血迹的摩托车,只是一个幌子。
撇开肉酱不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解释:吴雪已经把老人给毒死,老人躺在路上的时候就已经是尸体。一辆摩托车经过,从她身上碾过去。司机害怕医药费,便二次碾压试图让她死去。又因为这辆摩托车是司机偷来的——印证了摩托车主人的话——司机很放心地把摩托车留在现场,自己离开。
但我不能不去想,老人是被碾成了肉酱。如果只是为了把老人弄死以逃避天文数字的赔偿,根本没有必要把老人碾成肉酱。碾成肉酱需要时间,需要力气和毅力。我不相信肇事者会在紧急状况下,做出无意义的举动。
汽车。老人一定是被汽车第一次撞击以后,汽车司机为了隐藏撞击的伤口,想出用摩托车把她的尸体碾成肉酱的方法,这样,没有人会怀疑肇事车是摩托车以外的车。
她也根本不是被毒死以后再被碾压。假如是摩托车直接从尸体上碾压过去,同样也没有碾成肉酱的必要。碾碎的目的只可能是为了查不出汽车撞伤的痕迹。否则,作为替罪羊的摩托车,也没有任何价值。谁让摩托车上并没有撞击的痕迹呢?
至于为什么摩托车会和汽车在一起,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说,开车的人把摩托车装上汽车偷跑了。比如说,汽车里原本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开走了摩托。
所以当法医的报告说她是被毒死后再碾压时,我就明白那个法医撒了谎。
吴雪找人追杀我,很正常。如果是我,我也宁可相信死人才是真正不会说话的。我只是没想到那个杀手会撬开门进来,会刚好碰上我在发呆。而我的动作一向都很慢。
至于吴雪为什么那么轻易地认了罪,也只能怪她透露给我太多信息,以至于她在惊讶之下,相信是我骗了她,然后把所有的信息都透露给了警方——比如只对肝脏损伤和高性能液体色谱法。本来她可是认为没有人能抓到她的把柄。因此突然被审问,她便想当然地认为警方已经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实际上,我根本没有跟那群警察有什么接触。至于知道她被错抓时我为什么不去说出自己的怀疑,是我宁愿让她在拘留所里多呆几天。她毕竟是想杀人了。
而当那个倒霉的法医告诉我,是局长要求他这么做时,那天在现场的疑点浮现在我眼前。局长的车停得离草丛很近。距尸体约十米远。地上没有急刹车的痕迹。我开始相信,局长在到达现场之前,已经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对前方一无所知,他应该在空旷的路中央,在尸体的近处紧急刹车才对。
但是,局长的车上没有任何撞击的痕迹。
伪装法医报告对肇事者有直接的好处,警方会放弃对车祸的调查,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死因。局长不是肇事者,他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替肇事者做出了包庇的决定——下班假装发现尸体,亲自指挥现场。那位肇事者与局长的联系应当是非常紧密的,紧密得像尸体与蛆虫。任何一个人第一怀疑的,就是他的家人。
我潜入了局长家的车库,在车库的垃圾箱里,我找到了局长儿子车上缺失的保险杠以及车灯碎片,上面有还残留着指纹。我知道王兰那天穿的是毛衣,撞击必会把纤维留在保险杠上。
局长的儿子曾因偷窃而入狱。他很难对路旁还没熄火的一辆高级摩托车置之不理。
但我知道不能直接把它送到派出所去。饭馆里的议论告诉我,最近上头——难道不是局长的策动吗?——对刑警队特别关照。我不能冒着被局长截住或淡化的危险,把一个仅有的证据送回去。
这个时候,就要用上孝顺的慈善家梁柯了。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根本不是在为自己失而复得的母亲担心。在母亲出车祸后,他第一句问我的话便是:“快告诉我,那时我的妻子在干吗?”当他第二次要求我去调查时,他要我找出的是妻子杀害了母亲的证据;当我故意问他,我凭什么要接受他的委托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钱,而不是——比如母亲死得太惨,要查明真相等令人感动的理由。这可和他报纸上的论调不那么像。
你用什么样的心思猜度别人,你自己就抱有什么样的心思。因此,梁柯从一开始担心的就不是母亲的安危,而是妻子的有罪,以及他自己的钱。他没错,他的妻子吴雪就是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他故意选择了一个痴呆的老乞丐,他冷冷地看着她在半夜里追逐着年轻男女们的背影,口里流着白沫。他故意当街,当着所有人的面抱住痴呆的老乞丐痛哭,让所有的人也为他抹眼泪,相信他的真心可以感天动地。他故意在报纸上大谈财产问题,为了引诱他的妻子去杀害“母亲”。他是一个孝子,每一张嘴巴都这么说。
而我,和那个老乞丐一样,也只是他手里的工具。我监视着吴雪,等“母亲”被杀害后用我来证明吴雪的有罪。或者,不是杀害也行。只要能证明妻子对“母亲”不好,他就可以借此向法院提出离婚,而不毁坏自己的名声。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用吴雪的钱,把检测DNA的要求放到了警察局,又把电话打给记者们。结果支持了我的猜测。所以我找到梁柯,向他摊牌。而他吐露了秘密,也像吴雪一样信任了我对钱的爱意。
但我并不喜欢就这样结束。他利用了我,因此我不仅仅是要拿到他的钱,更想让他身败名裂。我去掉了音频文件里自己的声音,把它发到了记者们的电子邮箱里。
接下来的一步,是找到局长。我让他相信了梁柯雇佣我去杀他,并逼迫他雇佣我去杀害梁柯。
而我接受了他的委托之后,并没有做什么,只是在公寓里睡着大觉。局长得不到梁柯死亡的消息,自然会坐立不安。但他不能动用人力去寻找我,第一没有证据,第二,如果梁柯真的死了,而我不小心被目击甚至逮捕的话,他也会惹上嫌疑。
这个时候,是我把电话打到了局长和警员的办公室,向他们报告一个女职业杀手的所在地。不仅如此,我把电话打到了各家报社,让他们心潮涌动,各路兵马齐聚我如史前岩洞的公寓下。
只是我没想到自己的房间没有门牌,这幢公寓里许多门牌已经破损。我想让他们到的是隔壁的房间,然而这群人却闯进了我的房间。幸好,我并没有让他们以为我真的是职业杀手。我只是一个喝醉了酒的、人生无望的女人,我的房间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臭味。
在记者们和闪光灯们的目击下,他们看到了装着保险杠和车灯碎片的盖子,看到了我给他们的留言。我告诉了他们梁柯、局长共同伪造法医鉴定书的交易,是梁柯盼望自己的妻子有罪,而局长盼望自己的儿子脱罪。一桩多么美好的交易啊。
接着,你大可信任报纸上记者们痛心而讶异的报导。
我想像着梁柯在昏暗的病房里感受着刺骨的疼痛,想像着吴雪在精神病院里听着此起彼伏的尖叫,想像着局长躺在床上夜不能寐的模样,也想像了老乞丐的灵魂还会不会在那条阴暗的街上,追着正在尖声欢笑的年轻男女,伸出那只她放不下的碗,那只碗触碰着他们时髦的衣襟。我还想像了自己在空白的梦境里,头顶着墓穴的泥土的样子。
“一旦你死去了,躺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是躺在龌龊的水坑里,还是躺在高高伫立在山峰上的大理石宝塔里?你已经死了,你再也不会醒来,这些事你就再也不去计较了……再也不去思索你是怎样死的、死在何处这类龌龊的事情。而我现在却是这件龌龊事儿的一部分……过了不多久,他也要鲁斯提·雷甘一样,长眠不醒了。”
我的脑海里像字幕一样闪现着钱德勒《长眠不醒》的结尾,感到自己也只是一阵飘忽而短暂的呢喃。像那个被人利用的老乞丐一样,我的灵魂也伸着破烂肮脏的碗,一直追逐着我所得不到的该死的一切。
我转过身去,看见他们的眼睛和自己的眼睛,像是污水池里翻滚的泡沫。除了老乞丐的眼睛。
我走下楼去,想到梁柯到现在才得上肝癌,或许是吴雪残废的大脑里残留的痛彻余生的遗憾。
秦我
2007-2-14 12:11 初稿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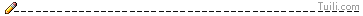
|
忽然间汽车吼出饥饿的鼾声
空气是受惊的马。现在,我坐在鲨鱼的胃里
夜晚恩赐我以灿烂的米糠
《明亮的困境》· 秦我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