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过指尖(漫过指尖) 漫过指尖(漫过指尖)
|
|
|
1 楼:
梦魇之遗失的爱
|
08年07月17日20点11分 |
清晨,天空还有些晦暗,我醒来。
俯身将脸埋进枕头里低泣了许久,老公阿源才缓缓地转过身:“怎么了?”语调中充斥着浓浓的睡意,不及我回答他的鼻息又均匀地响起……
很想推醒他,告诉他我的梦,可是手扬到半空终是没能落下来……
我轻抚着胸口那彻骨的余痛,踉踉跄跄地来到了书房电脑前,快速按下了电脑的启动按钮后,我清楚自己已经找到了最好的表述方式。
(一)
梦中的第一抹色彩是紫黑,那是我家黑桃木房门的颜色。
附在房门上作倾听状的粉色睡衣的雍肿身影,是怀孕五个月的我。
屋内的光线很暗,只有靠壁柜墙上的那盏嵌入式壁灯泛着荧荧的光,四周一片静谧,我能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心跳声,保持这个附趴动作已经有半个多小时了,可我依然什么都没能听到。
整整一个月了,我已经被各种莫名的不明来源的声响困扰了将近一个月了。
开始是拖鞋趿地发出的“沙沙“声,后来变成了有人向我们房间门缝吹气的声音,最近愈演愈烈,居然演变成了陌生女人的歌声,那歌声飘渺空灵在肃静寂聊的午夜极其渗透力,仿佛能刺入我的耳膜使破坏挠乱我的思维和神经。
每次,当我起身决定一探究竟时,那声音总是适时地嘎然而止,仿佛从未出现……
夜还在继续,我折回到床边。
睡梦中阿源安然恬静,我不禁伸手轻轻抚弄了一下他的前额,指尖触到了一丝凉凉的湿意——是冷汗,紧接着阿源无意识地拧了一下他那好看的卧蚕眉侧过身换了个睡姿。
阿源可能是做梦了,最近他实在太累了,为了负担家里日渐沉重的开支他又找了份兼职,我心痛之余转身从床头柜取来面巾纸,正当我弓身打算为他擦试汗水时,却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只见阿源缩着身子快速地抬了一下手腕眼角的余光正好瞄到手表的表面,这个动作间隔很短也就是二三秒的时候,可是阿源身后的我却看得一清二楚。
我呆呆地缩回手,坐到床边。回想最近发生的一切和刚才阿源怪异的举动,不禁要问:我的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四月的下半夜还十分阴冷,我裹紧了被子却怎么也睡不着,突然,感觉腹部有些隐痛,是小家伙狠踹了我一脚,估计是在责怪他妈妈没有好好休息影响了他的睡眠,我赶紧小心地捧着肚子上了床。
闭上眼睛恢复左侧卧位,在数了近五千多只绵羊后,我终于安然睡去……
醒来,身边已是空空如也,窗帘的暗红变幻成了浅浅的玫瑰红,又是一个明艳的四月天。
我知道这个时间阿源应该已经在单位的办公室里了,他的身边一定围着那么一两个刚来实习的漂亮女大学生,甜甜地叫他“蔡工”,或者手上还捧着刚泡的乌龙茶,因为阿源只喝乌龙茶。
我慢慢地踱到客厅,瞥见餐桌上的煎蛋和牛奶早已没了热气,怏怏地瞄了一眼后便去到了阳台,阳台上的植物有些湿气应该是阿源早上浇过水的缘故,光亮亮的颜色很是悦目,刚想伸手去触摸一下,猛地望到了楼下的绿化小空地处有两个人。
那是楼上房东阿秋的一家,于其说是一家不如说是母女俩,听她说她家男人原是本市一家知名酒店的老板,后来染上了毒瘾自杀了,财产清算后所留给她们的全部遗产就是这个城乡结合处的两套不大的房子,一套是我们楼上的602室,现在由她们母女住着,另一套则是租给了我和阿源。
命运之神似乎并没有因为男人的自杀而放过这个孱弱的女子,第二年的一次意外车祸夺去了她唯一的女儿小雯的双腿。
(二)
这时,绿化空地处的阿秋也发现了阳台上的我,她欢快地举起右手笑眸如花地呼唤我的名字:“小茹,快下来走走,今天的太阳很不错。”
我慌忙伸手回应,并示意自己马上下去。
刚出楼梯口,我的眼睛就被一道猛烈的阳光刺得无所适从,微合片刻后睁开,她们母女已经来到了我的跟前:“小茹,你应该多出来走走,孕妇需要多晒太阳。”
我笑着点头,刚想说什么的时候,发现轮椅上阿秋五岁大的女儿小雯正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盯着我,那眼神很冷很诡异,似乎在瞧一个怪物。我暮地一惊,转而向阿秋投去讪讪的笑,阿秋见状连忙转换话题说道:“小茹,有空的话请常上我家来坐,你知道我家平常冷清得很,这孩子也被这种清冷憋坏了,经常怪怪的。”
我马上表示同意并轻轻地拍拍小雯的小手和她示好,小女孩依旧没有说话,漠然地扭头将脸转向另一处,似乎在有意在躲闪着我。
就是这样稀松平常的一个扭头,却触动了我体内最脆弱的一根神经——熟悉、莫名熟悉的扭头。我哆嗦了一下,屏神凝望了她许久,暮地发现她的眉宇、鼻尖、嘴唇像极了一个人。他就是我的老公阿源,倏然两张一大一小的脸在我的眼前强烈地晃动起来,然后慢慢地靠拢……靠拢,最后融合在了一起。
我的头越来越重,直至失去意识……
穿越了一段漫长的黑暗之后,我发现自己飘了起来,飘呀飘……飘呀飘,不知道飘了多久,终于落在了一处风光秀丽的郊外,望着还泛着水泥新色的台阶我断定此地应该是一处刚开发不久的森林公园,举目四周山体峻秀草木芳菲。
实在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可是冥冥之中似乎有股力量在牵引我向山顶往上行去,四周静谧得出奇,仿佛这个貌似旅游风景区的森林公园只有我一个游客。
走了大概一百多米远的地方,左侧山间的竹林深处突兀地出来一对情侣,好不容易看到两个人影,我决意过去向他们打探一下这里的情况,近了……近了,我终于看清了这两人的面目,他们居然是阿源和我们的房东阿秋,只见他俩勾手搭肩兴致盎然地边走边笑,阿秋还时不时地用面巾纸帮阿源擦去脸上的汗水,俩人俨然一副羡煞旁人缱绻恩爱的样子。
我傻傻地呆立在原地,直至他们和我擦身而过。
没有人发现到我,虽然近在咫尺。
这难道就是我需要的真相吗?倾刻间我感觉四周天旋地转,山水失色,仰面痛泣了许久后,我选择了一处苍翠的悬崖纵身而下……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医院的病床上了,看到我醒来两目通红的阿源一把搂住了我:“小茹,你总算醒了。”
我推开他冷冷地说:“我饿了!”
阿源连忙从旁边的保暖壶里倒出一碗散着热气的红枣汤递给我:“小傻瓜,你就是因为没吃早饭就往外乱跑,血糖太低才晕倒的,这汤是阿秋刚刚送来的,快剩热把它喝了。”
“阿秋?”我暮地一惊手一抖汤碗掉在了地上摔成了两半,暗红色的汤水洒了一地。
“小茹,你没事吧!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阿源惊慌地看着我。
“我只喝牛奶,不喝红枣汤,赶快……赶快把那红枣汤给我倒掉。”我歇斯底里地大喊。
阿源无奈地看了我一眼,捧起那个暖壶默默地往病房外走去。
我闭眼做了个深呼吸,尽量使自己保持平和,因为我知道我肚子里的小东西他也在随着我的情绪的波动而波动着。
等了许多不见阿源回来,我只得自己起身倒水喝,这时病房外传来阿源低低的说话声:“她醒了,不过情绪还很不稳定。”
“在她昏倒前,一直死死地盯着小雯看,或者她已经发现了什么,都是我不好,明知道……”
“这不怪你,有些东西是注定的。”
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可我听得一清二楚。
(三)
突然,我的脑子清析得可怕。
那些纠结在心底不可解释的东西,在那一刻如同找到了一根串连起它们的线,一切变得顺理成章。
记起了去年阳春三月,阿源一眼看到阿秋和那套房子时成竹在胸立即拍板的样子,素昧平生的阿秋只租我们市价一半的租金却毫不介意的笑眸,还有那张令人心悸的熟悉小脸注视我的古怪表情,那种表情的下面到底包藏着怎样的夺父之恨?……
至于阿源的怪异行为,应该是在期待和午夜制造各种声响的女主角来一场亲密接触吧。
我全身冰冷,一股彻骨的寒意一直延伸到了每一根发丝和每一个细胞里,我的牙齿开始“咯咯”作响。
不行,我不能像梦中那样郁闷地自寻短见,我放他们一条生路,那谁又放我一条生路?
病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闪进来阿源一个人的身影。
“小茹,牛奶我已在水房热过了,快喝些吧。”阿源的声音柔和如初。
我知道此刻再没有比补充体力更为重要的事情了,我一把接过牛奶大口地喝了起来,可是没喝几口就被医院福尔马林的味道呛了出来。
“我要回家,我不要呆在这鬼地方。”我捂着胸口感觉阵阵莫名的恶心。
阿源见我态度强硬只得应允,不过叮嘱我无论如何得作一次全面检查才能离开,整整花了三个多钟头排队做B超、听宝宝心率、血常规……。
离开的时候,我依旧是一副面无血色浑身无力的模样,由阿源搀着一步一拐地上了他公司为他配的车。
回家后,阿源越来越忙,不过就生活的轨迹而言,倒真没和阿秋有任何的交集,一切又恢复了原位。
我则天天挂在网上,搜寻能和我共鸣的“资讯”。
终于,一本叫做《遗恨》的长篇小说深深吸引了我,小说讲述了一个由爱生恨最终感情畸变的悲剧故事,虽然故事的结构有些老套语言也很生涩,可是这并不影响故事所要体现的深义——背叛感情的人总会得到他应有的惩罚。
虽然,真正感动我的并不是故事本身,可是女主人公和我如出一辙的境遇总能给我痛彻心扉的共鸣,文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很喜欢:爱没有了,留些恨也是好的。因为有时候,恨才是终结一切烦恼根源的催化剂。
难道我和阿源的感情,真的非要像这本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要用非常的手段来结束一切吗?我的心蓦地颤了一下,来不及犹豫恨马上包围了过来,满满地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眼前突然莫名地出现了一副画面:阿源、阿秋还有小雯,三人围在一张饭桌旁,笑眼盈盈地用眼神交流着,虽然没有语言不过足够眉目传情。我刚纳闷是什么意寓?这时画面中又出现了一个人——是我。“我究竟是谁?”我伤心欲绝地喃喃自语,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你就是这张桌子的局外之人。
“不……不……阿源只爱我一个,以前是以后也是。”我捂住耳朵拼命地摇头,我知道我依旧爱阿源,或者说我仍对我们的未来抱有一丝希望。
(四)
正当我辗转难眠,心力焦竭地进退两难时,一个转折性的事件适时地发生了。
那是一个普通的午后,我正在房间睡午觉,突然一声闷响从我头顶的水泥板上弥漫开来。
我定定地坐起,迷迷糊糊刚睁眼就听到楼上传来凄厉的哭叫声,好像是阿秋在呼叫小雯的名字,断断续续地,一声高一声低。
难道是小雯出事了?是不是摔下来了?坐轮椅的总会摔下来那么几次,这也是常有的事情。刚想迈腿上去瞧个究竟,一个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低沉声音又开始说话:“由她去吧,罪恶的人无可救药。”我愣了大概七八秒钟还是收回了脚步。
暮地我发现头顶上的声音似乎在一瞬间消失了,变成了我家大门上急促的“咚咚”声。
我刚打开门阿秋便一头裁了进来,面色苍白地一把抓住我:“快,快打电话给阿源。”说完头一歪昏了过去。
为什么?为什么要找阿源?为什么不拔打120或者110?难道阿源是拯救人类生命的医生,还是救赎人类灵魂的耶酥基督。带着这些疑问我不自觉地往楼上走去。
楼上的房门微敞着,客厅里没有一个人,除了地上滚落的一袋散开的新购的日用品,四周都井然有条并无任何异样。突然我闻到一股香味,一股鲜美无比的浓香。接着厨房里传来咕咚鼓咕咚的声响,应声走近,我看到灶台上正煲着一锅浓汤,跳动的锅盖已经敞开了一小半,露出一小截的黑色。
什么东西?黑色的?我锁紧眉头慢慢地走近……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头发,人的头发,一大片一大片的,飘浮在汤面上。是谁的头发?难道是小雯?我的心猛地一怵逃也似地离开了厨房。
刚想迈出大门,心底满满的好奇心又强行将我拉回到了屋内,壮壮胆子我打开了其他的几个房间,卧室里空空如也,根本不见小雯和轮椅的踪影。最后我在卫生间的地面上发现了一滩新鲜的血迹,殷红的鲜血印着瓷砖的纯白显现出一种诡异的红,血迹的旁边放有一把锃亮的剪刀和一条黑色的塑料绳,绳子的一头被系在了洗漱盆的水龙头上。
这难道就是杀人现场吗?到底是谁被杀了?正当我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时,突然屋里的电话声响了起来,我鬼使神差地拿起了话筒。
是阿源的声音:“阿秋吗?刚才我来你家时,你没在。我看到小雯在坐在轮椅上宰杀乌骨鸡,她说要帮你做些事情,我女儿看来是真的长大了。对了,炖鸡汤的火我忘了关掉,特地打电话过来和你关照一声。不用担心小雯,我现在正带她去海洋世界玩呢。”
是我眼花?乌骨鸡看成了人的头发?血、剪刀、绳子自然也都是宰杀乌骨鸡时留下的。不过刚才的电话我绝不会听差,毫无悬念所有事实已能证明小雯就是阿源和阿秋的女儿,那么他所有晚归和忙碌的理由也就有了更好的解释。
阿源自说自话后看对方没有接话,又喂了好几声后只得挂了电话。
我离开了六楼,也没有回五楼。
只身游荡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一圈又一圈。
慢慢地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处公园,那是市中心最热闹的公园,四周聚集着一堆又一堆的来此消闲的人们,他们中有退休的老人、有刚刚学步的孩子、还有些面色窘困百无聊赖的年轻人。
刚刚在一个石凳坐定,一个二十来岁穿着阿迪达斯运动装的精瘦年轻人兀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大姐,你好像有心事。”
(五)
我仰面瞧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怎么你能算命?”。
“大姐,开门见山吧,命我是算不了可是我能搞IT,可以给一些需要帮助的朋友用科技的手段解决一些烦恼,比如你想知道别人的QQ记录盗取别人的邮箱密码或者入侵别人的网站……”
没等他说完,我便兴奋异常地问:“这么说你会盗号?”
“当然,这很简单,只需要植入木马。而且收费也是最低的。”年轻人讪讪地笑了一下,露出黄色的香烟牙。
“行,帮我盗一个Q号,需要多久?”想像着阿源呆在电脑前全神贯注的样子,我突然非常想知道他的QQ到底装有什么样的秘密。
“很快,要不了多少时间。”说着年轻人扭过头向公园右侧隐蔽的树丛处打了个手势。
没过多久,一个和年轻人同龄的男孩子拿了一台手提电脑鬼鬼崇崇地从隐蔽的树丛后钻出来,男孩将电脑递给年轻人后马上又走开了。
“这里的巡警很多管闲事,所以我们也只有将就着‘工作’。”年轻人利索地打开了手提电脑。
我侧过脸望了一眼周围:“这么明目张胆,难道就不怕巡警来找麻烦。”
年轻人没有抬头,拔弄着键盘说:“不怕,现在是他们交岗的时候,等他们上岗来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早完成了。对了,你要盗的是什么号”
“364734434。”报完号我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悲凉。
果然,没有多久年轻人便将电脑的屏幕移向了我。
“这么快?”我愕然地望了他一眼,说不清自己的感觉是悸动还是恐惧。
“看吧,这应该就是你想要的。”年轻人淡淡地说。
我的目光聚集在屏幕上,眼睛一眨也不敢眨。
排除了十多个异性QQ后,只剩下了一叫个秋的名字,是阿秋一定是阿秋,我的胸口一阵的憋闷,颤抖着打开了阿源和秋的聊天记录。
苍松(是阿源的网名):最近小雯的状况怎么样?
秋:还好,我更担心的是小茹。
苍松:我也是,她似乎发现了什么,以后还是不要让她接触小雯了。
秋:我也很担心,小雯的事情她迟早会知道。
苍松: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切不可让她知道,要不然她肚子里的宝宝也会受影响的。
秋:嗯,我明白。
苍松:我也不知道还能够瞒她多久,不过如果真相提前揭开,她一定会崩溃的。
秋:一定不能让她知道,她再也不能出意外了,再也不能。
苍松:不知道我们当初的决定是不是正确。
秋:什么?
苍松:选择住在楼上楼下。
秋:当初是为了你能看到小雯,我能看到小茹才决定的,我们的出发点都没错。
苍松:唉,是呀。真是辛苦你了,把小雯照顾得这么好。
秋:别这么说,自从爸妈在火灾中过世后,小茹小雯还有你都是我最亲的人。最近我老是梦到我和小茹小时候的时光,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她还像以前一样追着我叫我姐姐一刻也不愿和我分开。现在能为她照顾小雯,已经是我最满足的事情了。
苍松: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三年了,我记得小雯出事的时候只有两岁大,刚刚学习走路,老实说我实在想不到小茹会得旅行性精神病,要是可以预知未来,我是绝不会去驻外工作的。
秋:我也没想到,当时就是因为她的执拗说了她几句,没想到她真的去找你了,也不知道那段旅程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样刺激她的事情,居然会让她将小雯丢到了列车底下。
苍松:廖医生说过,只要过了今年十月,就满三年了。没有什么异样她就可以接受心理暗示治疗恢复失去的记忆,我希望在我们第二个宝宝出生的时候,小茹能健健康康。
秋:“会的,一定会的,小茹一定会挺过这关的。”
我盯着屏幕,突然往事如电影境头般汹涌而来,来不及细嚼回味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小茹,快来第二医院,要快。阿秋……阿秋快不行了。”
(尾声)
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发现阿源怔怔地立在我身后,发现我转身他幽幽地看了我一眼说道:“没办法,弗洛伊德说得没错,写作的人全有臆想症。”说完他一脸坏笑地向洗手间走去。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做梦,有时是晚上有时是白天。虽然梦的产生一直都有许多种不同的诠释,不过我一直认为每一个梦都有它的生命,它是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另一种潜能。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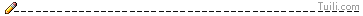
|
|
写呀写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