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g(catsanova) xing(catsanova) 
|
|
|
1 楼:
布朗神父:村里的吸血鬼(下)(译)
|
03年04月08日22点07分 |
布朗神父的下一个拜访对象是卡斯代尔斯—凯鲁小姐,如同预料的一样,卡斯代尔斯—凯鲁小姐给予牧师的儿子最无可救药的评价。不过,正因为言辞里集中了所有对这个年轻人的抨击,布朗神父反而确信这并非他言行的写照,只把这看作是一种常见的清教信条和流言的混合物。这位女士虽然自视甚高,为人却很亲切;她招待了来访者一小杯葡萄牙红酒和一片果仁蛋糕,就像所有人的祖姑妈那样。布朗神父在一篇有关道德与举止的普遍沦丧的宣讲开始前及时逃离。
布朗神父探险的下一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因为他隐没在一个卡斯代尔斯—凯鲁小姐想也不敢想的阴暗肮脏的小巷,既而又进入一间窄小的租借房屋,顶楼处一个高亢而滔滔不绝的声音使这里显得益发嘈杂……然后他再次现身了,带着一种近乎茫然的表情;人行道上他身后追随着一个神情激动的人。那人下巴铁青,身着已经褪成暗绿色的黑色礼服,声音雄辩地高喊着:“他没有消失!马尔特来夫永远不会消失!他在这里:他死气沉沉地在这里,而我活生生地在这里。但剧团其他的人在哪里?那个恶毒地偷走了我的台词的人、那个挖走了我的戏又毁了我的事业的怪物在哪里?我是第一个席卷票房的塔巴尔。他演了夏洛克——一个根本不需要表演的角色!我整个事业最好的机会!我可以给你们看报纸上关于我出演的弗尔廷布拉斯的评价……”
“我相信他们很出色,而且得到了应有的评价。”小个子神父喘着气说道,“我知道剧团在马尔特来夫死前就离开了村子。但这不算什么。的确不算什么。”接着他继续往前赶。
“他正准备扮演波罗尼乌斯。”兴致不减的雄辩家在他身后继续道。布朗神父忽然站定了。
“哦?”他很慢很慢地说道,“他正准备扮演波罗尼乌斯?”
“哈金那个恶棍!”那演员尖叫道,“追他去!一直追他到世界尽头!当然他已经离开村子了,没错。找他去,抓他去,见他的——”但神父已经消失在街尾了。
这场情节剧之后是两场平淡一些、但也许更加实际的访谈。神父先去了银行,与经理单独谈了10分钟;接着到那和蔼可亲的老牧师家里进行了一次合乎礼节的拜访。在这里,一切如同可以料想到的未曾改变,而且也似乎不会改变;挂在墙上纤细的十字架、书架上厚厚的《圣经》以及老牧师不加掩饰的对于人们日渐忽视礼拜日的哀叹都传达出一两丝来自一个更为严苛的传统的奉献感;但伴随着所有这些的又是一种不缺乏丝毫其应有的精细与黯淡了的华美感的优雅。
牧师也给了客人一小杯葡萄牙红酒,不过下酒的不是果仁蛋糕而是一块英国传统小甜饼。神父再次产生了那种奇怪的感觉:一切都太完美了,他似乎正置身在一个世纪以前。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和蔼的老牧师拒绝表现得更为可亲一些:他温和但执拗地坚持认为自己的道义感不会允许他和一个从事舞台活动的人见面。尽管如此,布朗神父放下那杯红酒时依然是面带感激的;随后他按照事先的约定与他的医生朋友在街角见面,他们由此一同前往初审律师卡尔维的办公室。
“我想你已经郁闷地转过一圈了,”医生开口道,“觉得这是个很乏味的小村子。”
布朗神父回话的声音高亢得近乎尖利:“不要用‘乏味’形容你的村子。我向你保证:这是个非同一般的村子。”
“我想我正在和这里发生过的唯一一件非同一般的事打交道。”医生评论道,“而这还是由外部的人带来的。也许该告诉你:他们昨晚已经静悄悄地完成了开棺的工作,今天早上我验过尸。简单地说,我们挖出了一具塞饱了毒药的尸体。”
“一具塞饱了毒药的尸体?”布朗神父颇有些心不在焉地重复道,“相信我,你的村子里还有一些远比这个非同一般的东西。”
一阵突兀的寂静,接着律师办公室古老的房门上的门铃被同样突兀地拉响了。两人被引见给那位从事法律业务的绅士,而后者又转而向他们引见一位头发花白、蜡黄的脸上横道伤疤的绅士,这显然是那老船长。
此时这村子的氛围已经几乎完全浸透了神父的潜意识,但他很清楚眼前的律师正是为卡斯代尔斯—凯鲁小姐这样的村民提建议的真正幕后人。尽管律师是个谨守古风的老人,但他还算不上老古董。也许只是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神父再次产生了那种奇特感觉:不是律师活到了20世纪初,而是他自己被传送回了19世纪初。嵌住律师的长下巴的衣领与领结做作得近乎被修剪过的枝条,但它们不仅外观整洁、剪裁也颇简洁。律师身上带着种老套的花花公子的风范;简而言之,他正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仪容保持得很好(虽然好得有些僵化)的人。
律师、老船长乃至医生都有些惊讶,因为他们发现布朗神父竟准备维护牧师的儿子、而不是像村里人那样为牧师感到悲哀。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年轻朋友很有魅力。”他说道,“他是个很好的交谈者,我想他也是个好诗人。马尔特来夫太太说他是个好演员。至少在这一点上那位女士是认真的。”
“事实上,”律师说道,“陶池村除马尔特来夫太太以外的居民更关心他是不是一个好儿子。”
“他是一个好儿子。”布朗神父说道,“最非同一般的就是这点。”
“见他的鬼!”老船长说道,“你认为他敬重自己的父亲?”
神父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对这一点我并不十分肯定。这是另一件非同一般的事。”
“你到底想说什么?”船长以水手的粗鲁口气叫喊道。
“我的意思是,”布朗神父说道,“这个儿子仍然在用一种很不可原谅的口气谈论他的父亲,尽管如此,他实际上尽到的义务只多不少。我和银行的经理谈过。因为我们正在秘密调查一起严重的罪案,在警方的授权下,经理告诉了我事实。老牧师已经从教区卸职了。不错,这里从来算不上他真正的教区。那些信仰随便的居民会像上教堂一样安心地去达顿-亚伯剧场,那里距离此地不到一英里。老人并没有自己另外的收入,但他的儿子挣了很多钱,老人一直受到很好的照顾。他招待我的葡萄牙红酒绝对是第一流的,我也看到了成排积着灰尘的旧酒瓶。我走时他正准备坐下来享用一顿如今已经罕见的旧式午餐。所有这一切都显然来自那个年轻人的收入。”
“好一个模范儿子。”卡尔维略带轻蔑地说道。
布朗神父皱着眉点点头,仿佛是被缠在自己设的谜团里:“一个模范儿子。不如说一个机械的模范儿子。”
就在此时,一个文员给律师送来一封未贴邮票的信。律师匆匆扫了一眼信封便不耐烦地拆开。在滑出的信纸上,布朗神父看到一串蛛网般疯狂缠绕在一起的字迹和一个签名“丰尼克斯·菲兹杰拉德”,随即开始猜想其他的狂乱字迹可能意味着什么。
“是那位经常纠缠我们的情节剧演员,”律师说道,“有些已经故去的哑剧演员是他的死敌,但和这次的案子无关。我们都拒绝见他,只有医生除外。医生真的看过他,最后认为他疯了。”
“不错。”布朗神父沉思着抿紧嘴唇,“我也认为他疯了。但这当然不意味着他的看法就不正确。”
“正确?”卡尔维尖叫道,“他对什么的看法正确?”
“关于这案子和老剧团有关的看法。”布朗神父说道,“你们知道这个故事中第一件让我困惑的事是什么吗?是‘马尔特来夫因为侮辱村子而被村民杀死’这种说法。验尸官居然能让陪审团还有那些容易轻信的记者都相信这种说法。他们对英国乡下人都缺乏了解。我自己就是个英国乡下人,至少我和那些芜菁一样都生长在埃塞克斯。你们能否设想一个英国农民会把自己的村子理想化甚至赋予人格、就像古时希腊的城邦居民那样?或是在村子的圣旗上画把剑、像意大利城镇中某个中世纪小共和政府的居民那样?你们有没有听到过哪个快活的乡下佬在哼哼‘只有鲜血才能洗去陶池之盾上的污点’?以圣乔治和龙的名义,我真希望他们能做到这些!然而,事实上我对这场所谓的争吵有另外一种解释。”
神父停了一下,似乎是在整理思路,随后继续道:“他们都误解了可怜的马尔特来夫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他不是在对村民说他们的村子不过是个小村落。他是在和一个演员说话。他们即将举行一次演出,菲兹杰拉德在其中扮演弗尔廷布拉斯,那个我们尚未见过哈金将扮演波罗尼乌斯,而马尔特来夫的角色无疑就是丹麦王子。也许另有演员想演这个角色或者有其他的看法,于是马尔特来夫愤怒地说‘你只能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哈姆莱特(译注: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和“村落”的英文同为“hamlet”)’,就是这样。”
马尔伯鲁医生目瞪口呆,似乎正在缓慢但并不怀疑地接受这个新说法。在其他人能开口之前,他终于说道:“你认为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
布朗神父猛地站起身,但语气依然平和:“如果这两位绅士允许的话,医生,我建议你和我去霍纳家一趟。我知道牧师和他的儿子现在都在那里。我希望你做一件事。我想村里目前还没有人知道你的验尸结果甚或你重新进行过验尸。我希望你能在他们都在场时告诉牧师和他的儿子这个案子的真相:马尔特来夫是死于毒药而不是死于棍击。”
马尔伯鲁医生有理由重新审视他对这个村子是否“非同一般”的怀疑。当他按照神父的安排去做这一切时,随后发生的一串事只能用人们所说的“难以置信”来形容。
塞缪尔·霍纳教长身着黑色法衣站在那里,高昂着他可敬的白发苍苍的头,双手按在读经台上;他经常在这里研读《圣经》上的文字,眼下虽然也许是偶然选择了这个位置,但这赋予他一种更威严的权威感。在他对面、蜷缩在椅子里的是他叛逆的儿子。哈雷尔抽着根廉价香烟,眉毛不寻常地紧皱着,完全是一副年轻无信仰者的典型样子。
老人亲切地招呼布朗神父就座。布朗神父坐下,目光温柔地望着天花板。但马尔伯鲁医生感觉他所要传达的重要消息似乎只有站着说出才能给人以足够的印象。
“我认为,”他说道,“作为这个社区某种意义上的精神父辈,您应该知道:那场旧日的悲剧又有了新的解释,也许是甚至更悲惨的解释。也许您还记得马尔特来夫的惨死,他被判定死于棍击,行凶的也许是村里某些对他怀有敌意的人。”
牧师摆了摆手。“主禁止我为任何类型的恶意暴力开脱。”他说道,“但是,假如一个演员想将他的邪恶带进这个淳朴的村子,他就是在挑战主的审判。”
“也许。”医生神情肃穆地说道,“但无论如何审判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我刚受委派对尸体复验过。我可以向您保证:首先,头部的击伤不可能导致死亡;其次,尸体中充满了毒药,这无疑是他死亡的原因。”
年轻的哈雷尔·霍纳丢下香烟,带着猫一般的轻盈与敏捷飞跃起来,最终止步在距离读经台不到一码的地方。
“你肯定?”他不敢相信地问道,“你完全肯定棍击不是致死原因?”
“完全肯定。”医生说道。
“好,”哈雷尔说道,“我早就等这一天了。”
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哈雷尔在牧师嘴边狠狠揍了一拳,随后将牧师像个脱了线的木偶一样直按到门上。
“你在干什么?”马尔伯鲁医生喊道;他震惊得手足无措,只剩下声嘶力竭的叫喊:“布朗神父,这个疯子在干什么?”
布朗神父并不动容,依然神色安详地望着天花板。
“我知道他会这么做。”神父平静地说道,“我还奇怪为什么他早先不这么做。”
“我的天!”医生高喊道,“我知道我们都错怪过他,但殴打他的父亲——殴打一个牧师、一个和平主义者……”
“他没有殴打他的父亲,他也没有殴打一个牧师。”布朗神父说道,“他只是在殴打一个扮做牧师的演员、一个敲诈钱财的恶棍,那人像吸血鬼一样依赖他生活了好几年。如今他知道自己不会再被敲诈了,他自由了。我不想过多谴责他的行为。何况我还很怀疑那个敲诈者是个囚犯。我想,马尔伯鲁医生,你最好把警察叫来。”
他们穿过房间,另外两人没有丝毫阻拦的意思:其中一人尚未从惊愕的茫然中回味过来,另一人则依然在交杂着解脱与狂怒的气喘中难以自控。不过,当他们擦身而过时,布朗神父曾回头望了眼那年轻人,于是这年轻人成了曾经在这张脸上看到如此不宽容的表情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他那句话说得对,”布朗神父说道,“假如一个演员想将他的邪恶带进这个淳朴的村子,他就是在挑战主的审判。”
“好了。”布朗神父说道。此时他已经和医生再次坐在正停靠在陶池村车站的火车车厢里。“就像你说的那样,这是个奇怪的故事,但我想这不会再是一个神秘的故事。无论如何,这故事在我看来是这样的。马尔特来夫来到这里,同行的还有巡游剧团的部分成员;其中一部分人直接去了达顿-亚伯剧场,他们将在那里演出一些19世纪早期的情节剧。马尔特来夫本人偶然出来游荡,身上穿着戏服,19世纪初典型的花花公子的打扮;另一个角色是一位守旧的牧师,他所穿的黑色长袍不那么显眼,就算有人看到也不过把他当作一个守旧的老头。扮演这个角色的是一个经常扮演老人的演员,他曾经演过夏洛克,还即将扮演波罗尼乌斯。
“第三个角色就是我们的戏剧诗人,他本人也是个演员,因为诠释哈姆莱特的方法而与马尔特来夫发生了争吵,但争吵的原因也许还有更私人的因素。我想很可能他从那时起就爱上了马尔特来夫太太。我不认为他们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我也希望他们现在能一切顺利,但他很可能会被马尔特来夫的气量惹怒,因为马尔特来夫是个颇为霸道的人,而且很爱挑起事端。在这样的一次争吵中他们动了棍子,诗人在马尔特来夫的脑袋上重重地打了一下,然后,按照当时勘察的结果,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像是诗人杀死了马尔特来夫。
“当时在场或者偷窥到了这一事件的还有一个人,扮演老牧师的那个人;于是他开始敲诈所谓的凶手,迫使他供养自己过上一个退休牧师的闲散生活。从事这样一种职业的人想这样改头换面是很容易的,他只需要继续穿着自己的戏服扮做退休牧师就可以。但他另有自己必须扮做退休牧师的理由。有关马尔特来夫之死的真实故事是这样的:马尔特来夫滚到矮树丛里,逐渐恢复了意识,试图走近某个住家,但最后还是倒下了;让他倒下的不是那记棍击,而是那位慈善的牧师一个小时前给他服下的毒药,那毒药也许就掺在一杯葡萄牙红酒里。我开始想到这一点是当我喝下那杯牧师给的红酒时。这真让我有点紧张。警方已经开始由此着手查这案子,但我不知道他们能否为这一环节取到证据。他们必须找到真正的动机;不过,显然这群演员彼此经常争吵,而马尔特来夫也树敌不少。”
“既然已经有了疑犯,警方一定会找到些证据。”马尔伯鲁医生说道,“我不明白的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疑的。究竟是什么会使你怀疑这个无懈可击的黑袍绅士?”
布朗神父淡淡一笑,说道:“就某方面而言,我想这是个特殊知识的问题;就更特定的方面而言,这是个职业问题。你知道,我们的抗辩者经常抱怨说人们对我们的宗教的现状一无所知。这个问题远比它表面上看起来有趣。英国对罗马教会知之甚少,这是真的,而且完全可以理解。但英国对英国教会知道得也并不更多;甚至还不及我了解。能够把握国教教义的民众数量之少会令你震惊,这其中很多人并不真正知道‘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究竟意味着什么,连他们日常行事的特点都不了解,更不必说与这两派相关的理论发展过程及其教义。这种无知你可以在所有报纸或是单纯的通俗小说及戏剧中看到。
“首先让我惊讶的事是发现这位可敬的牧师竟将所有的教义都搅在了一起。没有一个国教牧师会在每一件涉及国教的问题上犯错。他自称隶属古老的托利高教会派,但又自诩是清教徒。这样的教徒一般会自称‘清心寡欲’,而绝不会自称‘清教徒’。他公开承认畏惧舞台的邪恶,可他不知道高教会派通常不畏惧特定的东西,有这种畏惧的反倒是低教会派。谈到安息日时他的语气很像是清教徒,但同时他的房间里又挂着十字架。显然他对一个真正虔诚的牧师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他知道的不过是要表现得严肃、可敬、对世俗的一切享乐表示不满。
“这几天一直有种潜意识萦绕在我脑海里,一种我一时无法定型的记忆,然后它突然显现了出来:这是个舞台上的牧师。假使一个通俗剧作者或者老派演员要创造一个古怪的宗教人物,这样一个含糊而可敬的老傻瓜形象肯定是他们最方便的选择。”
“不要指责一个老派医生,”马尔伯鲁医生宽容地说道,“他对教内人士也了解不多。”
“事实上,”布朗神父继续道,“让我起疑的还有一个更单纯也更明显的原因。这与格兰治的黑女士有关,她被视为‘村里的吸血鬼’。
“很早我就有这样的印象:与其说她是村里的一个污点,不如说她是村里的一个亮点。她被当作一个神秘人物,但她身上其实没有神秘可言。她是最近才来到这里的,行事开放,姓名真实,面对有关她丈夫的重新调查也很配合。她的丈夫对她并不公平,但她仍坚持自己的原则,这说明无论就她的婚姻还是就普遍正义而言她都有无可愧疚之处。正因为同样的原因,她选择住在自己丈夫丧命处旁边的房子里。与‘村里的吸血鬼’同样无辜与坦诚的是所谓‘村里的丑闻’:牧师的放荡儿子。他同样没有试图掩饰他的职业和他与舞台界过去的交往。这也是为什么我不会像怀疑牧师那样怀疑他的原因。不过,我想你已经猜到我对牧师产生怀疑的最真实也最重要的原因了。”
“不错。我想我知道。”医生说道,“这也是你提起那位女演员的原因。”
“是这样。我是说牧师钱财来源的稳定性取决于不见到这位女演员。”神父说道,“但实际上并不是他拒绝见到她,而是拒绝让她见到自己。”
“我明白。”医生点点头,“如果她见到可敬的塞缪尔·霍纳,她马上会认出这就是那位用虚伪的牧师外表掩盖自己恶劣品行的很不可敬的哈金。算了,我想这就是这部单纯的乡村田园诗的全部内容了。不过,你得承认我信守了诺言,让你看到乡村里比尸体更令人不寒而栗的东西,哪怕这尸体是塞满了毒药的。用敲诈者的身躯塞满的牧师黑袍多少还是值得一提的,我们这里的活人比你那里的死人还要恐怖。”
“没错。”神父说道,同时把自己的身体舒适地靠在垫子上,“要说火车上称心的旅伴,我还是更喜欢尸体。”
(完)
p.s.最后一段原文是医生说的,但感觉应该是神父的话,所以擅自改了。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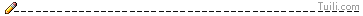
|
|
Ruhest du auch.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侦探推理 > 欧美名家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侦探推理 > 欧美名家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5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