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蔡(老蔡) 老蔡(老蔡) 
|
|
|
2 楼:
Re:【连载】《草莓采摘者》(作者:...
|
12年04月17日20点50分 |
1
那是人们可以嗅得到酷热的一天皮肤被太阳烤焦了,一运动就会从所有毛孔里流汗;那也是让他抓狂的一天,那天最好谁都别碰上他。
那样的他,周围人已经慢慢习惯了。他们让他安静地工作,不跟他说话,甚至在他从旁边走过的时候会压低声音。
他不理解为什么会有那种一直喋喋不休的人。他们根本不去区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只是简单地用他们普通的、愚蠢的、激动的话将所有的事情抖搂出来。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以退回到自己的世界中的方式来对付这种情况。他喜欢看对方的嘴唇动着,声音却丝毫不能进入他的耳朵,就像一条鱼,他想,像一条旱地里的鱼。
以前他会因为这种拒绝跟外界交流的方式遭到毒打,而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去关注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他了。绝大多数人就像他们的话一样,贫乏、愚蠢。
还有一个小时就吃午饭了,接下来他会迅速解决掉午餐,然后继续工作。
当全神贯注的时候,他知道那种不安来自哪里,他知道为什么他的手会颤抖,就像现在一样。
啊,上帝啊。他压下一声呻吟。有两个女人扭过头来看他,他几乎不认识她们,只冷冷地瞪了她们一眼,两个女人垂下了眼睛,转过身去不再看他。
天上的太阳是唯一的光明。
他想:让我体内的这种想法燃烧吧,求你了,还有这种感觉。
但是太阳只是太阳。
它没有满足他愿望的能力。
这种能力只有仙女才具备。
年轻,美丽,且纯洁无瑕,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只属于他一个人。
车子行驶中迎面而来的风将新鲜草莓的香气吹进开着的车窗,还有这一年过早到来的炎热。裙子沾到我的腿上,我的上嘴唇挂着汗珠。虽然我爱我有毛病的旧雷诺,但是在某些日子里我也强烈渴望拥有一款带空调的新车。
转过弯儿我就能看到他们了田野里的草莓采摘者,他们或弯腰或小心地沿着草莓垄之间的空地行走,胳膊上挎着装满草莓的箱子。他们让我想起了摘棉花的奴隶。一望无际的绿色平地上的彩色圆点,被太阳烤成了棕色。
他们是季节工,很多来自波兰,很多来自其他的什么地方,还有很多来自德国最偏僻的角落。最后的冒险者,一年一次的入侵,村民们为此关门堵窗。
每个晚上,陌生的男人女人们、姑娘小伙子们在村子中心的泉边集合,他们抽烟、喝酒、聊天、大笑。他们与世隔绝,从不跟邻居们打招呼,也从不跟他们笑。
这正应了某句谚语:你如何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么对待你。村民们种下了不信任的种子,现在收获的是他们应得的回报。
我开车回家,顺着长长的蜿蜒的山路一路向上,车轮压在白色砾石上面咯吱咯吱作响。像电影里一样,我想,一切都太过完美,让人觉得不像真的。那么,如果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只是在做梦该怎么办?
只要一靠近这栋房子,就会闻到这里的每一个细节中隐藏的钱的味道。以前的水磨坊被斥巨资仔细地修葺过。在内部布置上,建筑师甚至还考虑到了在溪流旁边开一个小口,通过一条狭长的穿过门厅的小水沟将溪流引到里面来。
阳光在经历过两百年风雨的红色老砖上嬉戏,让砾石层闪闪发光,然后又转到侧房的玻璃面上,看起来像是科幻小说家想象出来的幻景。
这是我母亲的房子,每一次拜访我都会被它的美所重新吸引。
我打开门走进大厅,感觉到一阵沁人心脾的凉意。还有我们的公猫埃德加,它的名字归功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母亲非常喜欢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
我抱起它抚摸着,地上顿时落了一片猫毛,难道它还在掉冬天的毛?我重新把它放到地上,它舔了舔肚子,趾高气昂地从我前面绕到台阶那边去了。
屋里的所有东西也都非常精美、非常珍贵,都是请有经验的人布置的。太阳将午后柔软的阳光透过高窗洒进大厅,台阶上的木头在阳光里闪闪发光。水磨石地板上的藤沙发、简单涂抹的白墙和窗子的圆形僧侣壁龛则都勾起人们对意大利的无限向往。
仅台阶本身就已经称得上是艺术品了,看起来简直像是悬在空中一样,做这个楼梯的木工在用最少的材料产生最大的效果方面非常有名,而且做得很成功。顺便提一句,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每一个房间、每一件布置的物品,我母亲选的都是最好最贵的,她付得起。
走到楼梯的尽头,埃德加径直穿过上面的大厅,它知道我会先去看我母亲。
她的房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可能她睡着了吧,我轻轻地推开房门。
母亲坐在写字桌前,桌子上面摆了一摞纸,眼镜架在鼻子上。她转身朝向我,面带微笑:“洁蒂,太好了!”
我母亲是作家,确切点说是侦探小说家。她为皮彭布林克出版社写了黑色系列,而且成就斐然。
自从我母亲放弃她和她的女人圈子里所理解的真正的文学之后,她的书就开始卖得像刚出炉的小面包一样火了,其间这些书被译成了二十多种语言,而且有多家公司争抢电影拍摄权。
“你先坐一下,我马上就好。”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打扰我母亲,除了在她描述她的想法或记录她的灵感的时候,关于这点我早就习以为常,也就不再觉得别扭了。原来可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一直觉得,对她来说她的文字要比我重要得多。
埃德加已经跳到沙发上等着我过去坐下了,它蜷缩在我腿上,闭着眼睛,打着呼噜,爪子轻轻地抓着我的大腿。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母亲出名之前的生活,那时我们住在布鲁尔的一栋行列式房子里面,前面的庭院看起来就像精心修理过的家庭墓地,种着针叶灌木、杜鹃花和一年生植物,到处都有清水汩汩地流过泉石,流到睡莲池里面,泉石已经被冲刷得很干净,池里的金鱼有手掌那么肥。
底层被常春藤掩映的窗子后面是我父亲的办公室,家门的右边,大概齐眉高的地方,挂着一块黄铜的牌子,上面写着“提奥?魏因加特纳,税务顾问”。牌子被擦得锃亮,父亲的很多顾客在按门铃之前都会先观察一下牌子的材质。
我们有一个钟点工,每周两次帮忙将房子大扫除一遍,每月会有人过来擦一次窗子。而母亲的工作就是写作、写作。
除了她一楼工作的房间,她最爱的能够证明自己的地方就是花园,她的花园看起来像是《居家与园艺》里的一个完美的样品,修剪的部分与杂草丛生的角落混搭得恰到好处,这正是时下园艺杂志中流行的。
母亲用园艺工作来治疗她的写作危机,或许有时遇到问题的时候她更想跟我父亲谈一下,而不是将它们埋到地里或绑到搭棚上,然而父亲对母亲文字上的问题和她所从事的语言工作提不起丝毫兴趣。
一旦提起母亲的工作虽然这种情况极少他就会称其为“没完没了的抄写”,而我母亲则被他称作“抄写员”。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会善意地挤一下,所以别人也不会当真。“作家”这个词他是不会说出口的,因为那样的话就意味着他开始把母亲的工作当回事儿了。
即使母亲第一次在脱口秀上出现的时候,记者为了拍照片和电影短片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他的态度也一直没变。
然而等出版社结完帐之后,父亲便不得不开始对母亲的工作刮目相看。这笔钱让我们添置了很多东西:一辆新宝马、父亲办公室里一套现代实用的设备、母亲的新电脑和渴望已久的温室。
母亲的写作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很少,它就像附属品一样,很少有我们的参与。
什么时候如果她在厨房出现,那就意味着她新的手稿又完成了。几周后她的审稿人便会过来,他们坐在温室里讨论她的稿子,把稿子分发得到处都是,搞得都没地方落脚,却从不会弄得乱七八糟找不到。
稍后清样、封面设计等便会寄过来,再什么时候成书也会寄过来。
母亲需要写作,为了维持日常生活,就像她说的,一直都是这样的。可能那时候的写作对她来说更加重要些,因为除了她自己的日常生活外,还有我父亲的日常生活需要维持。
父亲不喜欢惊喜,他在一个完美的家和一份完美的工作中经营着他完美的生活,在我看来,有时候他就像住在一间巨大的玩偶屋中,那里的一切从来不会失去秩序,那里的一切都完美地待在它们该待的位置上。
与此相反,母亲则天生一切都乱七八糟,她的玩偶屋肯定在她还小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恐怖了,所以她将收拾房子的事情留给别人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
她越来越多地将精力放在花园上,这是她自己的、容易管理的、有限的宇宙,这里的一切可以任由她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支配,这里的经营成果显而易见,错误也很容易改正。
写作也是同样的道理。母亲能够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里面的人物和命运完全由她一个人支配,有人生,有人死,而操纵那根线的就是我的母亲。
这些就发生在那扇关着的门后面,在她的寂静的小工作室中。有的时候她会说起这些,那时她的眼中便会闪着火花,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她会将她的写作经历留给自己,与我们则谈些别的话题。
有一次,一本画报把我母亲刻画成一个被写作完全占有、已经学会很好地隐藏自己欲望的女人,她的生活太少,而在她的故事中她则虚构出另外一种生活。
另外一种生活!或许那种生活中本来可以有我父亲的陪伴,如果父亲愿意的话。但是他不愿意。
那么我呢?没人问过我。
母亲也会逃避到朗诵会的出差中,一整个星期的时间都在路上,从慕尼黑给我打电话,从汉堡给我打电话,从苏黎世,从阿姆斯特丹。我们的电话旁边一直有一个宾馆的名单,她就在名单上的某家宾馆里面“妈妈:能联系到的地方……”
在她消失的这段时间,我们的钟点工变成了女保姆,从早到晚待在我们家,负责解决掉家里积攒下的所有工作。她也给我们做饭,她的家常便饭让我父亲在这段时间里超重十公斤。
母亲出名了,我在学校里的地位渐渐变得特殊起来,甚至有些老师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尊敬。我开始出售母亲的亲笔签名,以此带来的收入相当可观。
每个晚上,当房间里的影子开始摇曳的时候,我便开始想念母亲了。我并不是想要她一直在家里,恰恰相反,我只是习惯了听到她上楼或下楼的声音、她低声读手稿中某一段的声音、她打电话的声音。同样我也想念她香水的味道,像一层看不到的薄雾飘在她停留的或刚刚离开过的房间里。
我们有钱了。父母买下了艾克斯哈姆两万平米的老水磨坊。水磨坊坐落在风景保护区,宁静安逸,很田园。而且他们还请了一位有名的建筑师进行修葺和改造工作。父亲本来更喜欢布鲁尔城郊的一栋别墅,却没有买到。他还给自己请了一位女秘书。
她叫安琪,人看上去跟她的名字一样,三十五六岁,金灰色的马尾,手上戴满戒指,超短裙紧裹在身上。母亲把她所有空闲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建筑工作上,父亲却一点空都没有,因为他的时间都用来和安琪一起埋头工作了。
那段时间我在随便什么地方到处游荡,荒废学业。之后的一次打击让我长大了,那时我十五岁。
一年以后我父母离婚了。父亲没有随我们搬进收拾好的水磨坊里面,他留在了老房子里,和已经怀孕的安琪一起。
“好了,”母亲摘下眼镜,“你来得正是时候,我正想喝杯咖啡呢,你有时间一起吗?”
“只要你愿意。我真的没有打扰到你吗?”
她放下笔:“打扰到了,但是正是时候,我正好写不下去了,电脑我早就关了。像兔子盯着蛇一样一直盯着最后一句话,然后忽然发现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你知道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吗?”
母亲没有等我的回答,演讲式的提问是她的特色。她站起来,俯身吻了我一下。
她香水的味道,跟她的声音和皮肤的温度一样,让我感觉很熟悉。Calypso①,她从来不用别的款,这款香水柔和、清新,有夏天的味道,是母亲在一个化妆品店掺的,她特意将香味混在一起,然后自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
这是自从有钱之后,除了在一些从来不戴(因为她觉得看起来太引人注目)的比较别致的戒指、项链、手镯上花费一部分钱之外,她允许自己做的唯一一件奢侈的事情。
“有什么不对吗?”她捋了一下剪短的黑头发,上面已经夹杂着缕缕银丝。
“恰恰相反,”我微笑着,“你看起来棒极了,就像一直以来那样。”
她挽着我的胳膊拉我出门:“你也是。”
一个很明显的谎言,但是或许她没有注意到自己对我说谎了,又或许她在对自己说谎,说服自己,我很漂亮,长得像她。
然而我并不是这样的,而且我也从来不想这样。我不想用我的独一无二去换取这个世界上的美丽,即使我的独一无二没什么特别的。我就是我自己,而且这比某些人所声称的更要坚定。
我们向楼下走去。阳光洒满整个厨房的地板。莫莉,我们的母猫,伸着大大的懒腰,身上的黑白图案就像棋盘状的瓷砖。“莫莉”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是我给它取的,没有借助于什么东西,也没有谁给我什么灵感。见我来了它对我喵了一声,站起来在我的腿周围来回蹭了蹭,对我表示欢迎,然后便和埃德加一起穿过开着的阳台门消失在花园中了。
母亲在那台已经用了有些年头的压缩咖啡机旁边煮咖啡,我又一次发现,她跟我外祖母越来越像了。她经常会因此而生气,因为外祖母跟她水火不容,而且两人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
“你的新书什么时候完成啊?”我一边问她,一边坐到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桌子沿儿上。
“会花掉我生命中的几年吧!”母亲随时能够将最富有戏剧艺术的语言与最平庸的技巧联系起来。她专心致志地把咖啡杯、糖和一个盛着橘子小饼干的碗放到一个托盘里,一起端到露天阳台上去。那个托盘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或者见过但是没有注意过。“你在这儿住的那会儿,我更能够集中精力写作,现在我需要我们生活中曾经有过的安安静静的规律生活。”
“那你就不需要我?”
话几乎还没出口我就已经后悔了,在我名人母亲的生活中,我难道一直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组成部分?她根本不需要我这个事实难道会一直让我这么痛苦?是不是对她来说谁做她的女儿都一样,随便哪一个,可以任意换掉?
“忘了我刚才说的吧!”我挥挥手,试图把刚才的问题抹掉,“我只是随口说说。”
她看着我,很受伤的样子。
“洁蒂,你就不能改掉你这过度敏感的毛病吗?”
而这恰恰是她的毛病,有时候她可以为了某个音节和你争论上一个小时。
我把自己扔到花园的椅子上,靠着椅背深深地吸了口气。每次当我后悔从这儿搬出去的时候,都仅仅是因为这边的风景目光越过起伏的田野,能够看到附近农夫在田野上放牧的羊群,偶尔某处会立着一棵弯曲、倔强的果树,像是被遗忘在了草丛中。
没有人碰过这片风景,庆幸的是,就连我母亲也没有一时突发奇想,自己或请人在这儿修一个公园式的花园。她跟我一样,也感受到了那种魔力,所以没去破坏它。
潺潺的溪水声让这种田园生活变得更加完整,我两手交叉枕在头后,闭上了眼睛。
“你什么时候继续上路?”我问。
母亲一直等到我睁开眼睛才回答我:“只是一些单个的作品朗诵会,你是知道的,夏天的新闻淡季我一般都用来写作。”
新闻淡季!一切都要围着她的写作转,甚至连季节都是。她跟我父亲分开以后,写作对她来说就变得更加重要了,那似乎是她的某种保护,让她可以躲避这个世界、躲避孤单和内心的某种情绪。
我比以前更加仔细地看着母亲,如果她所呈现给大家的一切都只是表面、只是一副完美的铠甲呢?我感觉到了她神经的能量,这种能量仿佛在桌子上流淌,她每开始一本新书都会这样,伸出她的触角,去触摸每一个人、每一句话、每一点噪音、每一声响动和每一种气味。
在这样的时候跟她说什么都是白搭,因为虽然她的人在,但她的思想早已经去了别的什么地方了。
“这篇小说很特别,”她犹豫着说,“第一章已经写完了,可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找到主角。”
我点了点头,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她。而且每次跟我谈起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她通常也不会等我的回答,她只是在自言自语,把她的倾诉对象当成一面镜子。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不!这是一个错误的童话,我没有成为白雪公主的天分,一句独一无二的有毒的话就可以让我窒息而死。
我们沉默地喝着咖啡。
“你来有什么事吗?”母亲问。
好问题!我来有什么事呢?可能我原本是知道的,但是这期间我给忘掉了。
死者赤身裸体躺在树林里的矮树丛中,脸部朝上,胳膊从身上耷拉下来,她的右腿轻微弯曲,左腿直伸着。
她的头发被剪掉了,有一缕散落在肩膀上,剩下的被风吹走,缠在周围植物的茎上或粘在了粗糙的树皮上。
她的眼睛瞪得很大,盯着天空,似乎她在死前的那一刻非常惊讶。
发现她的是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兄妹两个,男孩儿十岁,女孩儿九岁。父母不让他们在树林里玩儿,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去了,而为此也受到了严重的惩罚用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的一幕景象。
他们大喊着跑开,边喊边跌跌撞撞地跑过草地,爬过篱笆,钻过铁丝网。他们正想从砖瓦厂抄近路走的时候,被一个工人拦了下来。他听他们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讲完了事情的经过,于是喊来了警察,又把孩子们送到警察局办公室。警局的女秘书给两个孩子冲了杯可可,并和他们的妈妈取得了联系。
经调查证实,死者是位十八岁的女孩儿,被强奸过,身上有七个刺孔,仅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致命的,直达心脏。
死者来自豪恩吉尔辛,与埃克斯海姆相邻,是一个还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学生,在现场的一个保安警察可以确认她的身份。因为认识女孩儿的父母,所以他表示已经做好准备,由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母亲在门口就晕过去了,她丈夫把她扶到客厅的沙发上,在她腿上盖了床被子,然后拍拍那个警察的肩膀,向他要一杯烧酒。
一个人在受到打击后是会做出类似的事情的,他们会做平常很少做的事儿。那个警察遇到过一个女人,她在听完丈夫出车祸死了的噩耗之后,走到厨房,倒了一碗凉鸡汤一口气喝下,好像很久没吃过东西一样。
女孩的名字叫西蒙,西蒙?埃德莱夫。整个地区的人都参加了她的葬礼,那是豪恩吉尔辛所经历过的最大的葬礼。
十二年级所有的人都出现在了葬礼上,女孩们用手绢捂着嘴,男孩们则偷偷用手背抹着眼泪。所有人都还处在震惊之中,死亡来得太突然、太出人意料。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凶手让人绝望恐怖的犯罪手段。
这种类似的恐怖案件以前大家也经常听说,但那些都离他们很遥远,一旦这种事情真的发生在身边的某个人身上了,他们似乎才开始考虑,到底哪儿才是安全的。
葬礼大厅中奏的是死者的一个女友精心挑选的音乐,旋律连同忽明忽暗的烛光和透着死亡气息的鲜花一起填满了整间大厅,带着一种绝望的悲伤。
外面阳光明媚,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是一切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据布鲁尔警局警长贝尔特?梅尔泽解释,此次十八岁女孩儿西蒙?埃德莱夫的谋杀案跟一年前德国北部耶弗尔和奥里希两地发生的年轻女性被谋杀的案件有极大的相似性。两起案件迄今为止都未破获。考虑到案件调查工作的需要,梅尔泽警长不便透露详情。
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长时间地失眠。他喜欢这种在半睡半醒之间袭来的噩梦,这让他有点事儿可做,但同时他也痛恨害怕它们,而此刻他正在害怕。
他拼命地让自己想点别的什么事儿。
但一切都是徒劳,画面如同回旋飞镖一样去了又回。
他仍然能感觉到那种愤怒,从未有过哪种感觉如此强烈。
他想:女孩,你为什么总是欺骗我?
走近看,她们根本不是什么仙女,连真正的美丽都算不上。她的声音在害怕的时候听起来很尖,像鸟的声音,这样的声音让他疯狂,他痛恨听起来透着恐惧的虚弱的声音。
他痛恨害怕时出的冷汗。
她的手当时又湿又滑。
事实上他不应该真的相信仙女,毕竟他已经不是孩子了,而且仙女应该有更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只会讨他开心。
她应该像一个仙女,就像小时候让他着迷的童话故事中的仙女一样,身材苗条,头发柔软有光泽。
美丽。
大眼睛,长睫毛。
从远处是看不到细节的,只有站在半米之内的时候才能看到,可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就已经太晚了。他总能发现一些让他觉得不可理喻的意外,仅仅是错误位置上的一颗色斑,就已经足够破坏整幅图画的效果了。
耶弗尔的女孩身上有一股烟味儿,她甚至递烟给他抽。她卖弄风情地笑着,头向后仰把烟吐到空中,完全没有意识到她早就给自己判了死刑。
他呻吟着翻了个身。他很庆幸自己没跟其他农民住在一起,而是在这个小旅馆里面给自己租了一个房间。房间很小,条件很差,靠着浴室,是一个所谓的湿间,里面窄得几乎让他不能活动,而且上面就是屋顶,白天被太阳烤过后晚上房间里会很热,从窗子可以看到邻居家的烟囱。但是这边的租金他能付得起,而且他也可以不用放弃他的自由。
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安全地做梦。
他的梦不适合在有很多床的房间里做,那种经常吓得他浑身是汗的不安是很难隐藏的,同时他也害怕自己睡着的时候说梦话。
不,这儿已经好多了,接近完美。
要是他能睡着的话该多好啊。
他需要用睡眠来让自己面无倦容,以应付白天的时间。很显然,白天的时候,条子也会在草莓采摘者中间来回打探,他们会再回来的,只要他们有一点线索。
他翻过身来仰面躺着,手交叉垫在后脑勺上。
但是他们是找不到什么的。
他们是抓不到他的。
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
黑暗中他微笑着,很快进入了梦乡。
【未完待续】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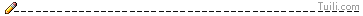
|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http://www.tuili.com
| .&______~^@^~______&. @
-- @ -- "w/YYYYYYYYYYYYYYYYYYY\w" @@@
| Y--Y--Y-----Y--Y--Y @@@@@
p-p_|__|__|_____|__|__|_q-q @@Y@@
__________________[EEEEM==M==MM===MM==M==MEEEE]-______|_____
推理之门 老蔡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侦探推理 > 欧美名家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侦探推理 > 欧美名家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5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