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V(聆听) VV(聆听)
|
|
|
1 楼:
多指教 :)
|
02年01月18日20点05分 |
从柯南道尔到克里斯蒂
――传统侦探小说的认知与批评价值重现
侦探小说是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但它在文学研究领域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自居正统、捍卫所谓主流文学的评论家对通俗文学研究嗤之以鼻,甚至羞于承认对这种文学类型的关注,通俗文学在他们看来只是生活中的一项娱乐活动而已。诗人兼评论家W.H. Auden曾承认“对我来说,和其他很多人一样,阅读侦探小说就像是嗜好烟酒。”
1、侦探文学研究的现状
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于洪笙在评论我国侦探小说发展状况时说:“…专业作家很少进行这类文学样式的写作,认为这类小说不登大雅之堂,更缺乏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外都存在着通俗文学本身强大的生命力与通俗文学领域理论研究的空白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本不多见,且多数仍停留在对其情节设置和人物刻画的美学评说上。以侦探小说为例,David Geherin可算该领域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也主要研究后现代侦探小说的“硬汉侦探”形象特点; Grossvogel(1983)把克里斯蒂小说的持久魅力部分地归功于侦探形象和改编电影的成功。 应该说这些理论研究中对侦探小说的深层结构、文体特点和读者在阅读中的理解机制研究较少,为重现侦探小说的批评价值,本文拟从读者认知角度来研究通俗文学受欢迎的原因及对主流文学的借鉴作用。
近年来,鉴于通俗文学在大众文化中的重要影响,许多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通俗文学作品的文体特点。Wagoner(1986)对克里斯蒂的生平以及各个时期的作品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而且在第六章还以“形式的游戏”(Games with form)为题对克里斯蒂三十年代的小说进行了互文性分析,强调了其小说之间的主题互借现象,把小说基本要素(如人物、背景)的变换归结为克里斯蒂小说受欢迎的原因。朱国华在《文艺研究》(1997,6)发表《略论通俗文学的批评策略》,建议将通俗文学纳入严肃的学术范畴之中,采取一种批评的策略,在以人文尺度把握文学精神之外,还要对通俗文学的内部规律进行探讨。但总的来说,从小说的文本功能和读者心理认知角度对这种文类的总体把握还是一个空白。朱国华还进一步指出探讨通俗文学的形式和技巧应该从其功能着手,其美学价值倒在其次。本文以传统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从文体特点及其相应变化的理解认知模式的角度出发,试图探讨侦探文学的批评价值。
2、传统侦探文学研究的新视角:理解认知模式的类型
侦探小说的鼻祖是爱伦•坡,但传统侦探小说的集大成者当推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柯南道尔以短篇小说见长,他塑造的侦探形象福尔摩斯已成为神探的象征和代名词。阿加莎•克里斯蒂则擅长把握长篇小说的宏大结构,她的侦探波罗和马普洱小姐作为业余侦探也是深入人心,与性格特异、具有刻板专业精神的福尔摩斯相比,前者更具亲和力。这两位作家可以说代表了传统侦探小说的最高水平,但他们在作品中体现的差异也是巨大的。主题类型相同而风格有异的文本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读者的呢?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又是怎样有意识地对读者的认知过程进行限制和引导的呢?这些技巧对于主流文学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呢?侦探小说的批评价值何在?带着这些问题,本文试图探询读者在理解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时认知模式上存在的差异,以期对这种文类的理解机制和批评价值有进一步的了解。
对阅读中理解认知模式的研究目前比较流行的大致有两种。第一个是自下而上法,即bottom-up 模式,该模式认为阅读理解是一个线性的信息流动过程,以文字为基础处理信息(text-based), 不考虑读者和语境的作用,即阅读者在没有外部因素干扰和帮助的情况下, 只从文字、句子和语篇上理解文章含义。读者相应的理解认知过程为解码文字,读取信息,然后存储记忆。
第二种模式是Goodman提出的“心理语言的猜谜游戏”这一著名假设。他认为作者用文本表达自己的思想,传达一定的信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利用心理语言模式,力图重现作者的意图。这种模式又被称为自上而下法(top-down模式)。 它强调依据知识(也就是图式)处理信息。“图式”(schema)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认识构架,使信息有条不紊地存储在长期记忆里。认知者对于世间典型场景的认识和知识在头脑中被分门别类,并以一定的命题网络,即图式网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提供阅读时所需的参考。除此之外则由新的具体信息来填补空白。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并非如第一种模式所说被动的输入和编码,而是对已有的心理表征有意识的进行组织和建构,也就是说,阅读者依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在阅读时已经有了一个预测和假想,阅读过程是一个在阅读和原假想之间不断验证、磨合的循环过程。
当然,没有自下而上的文字理解基础,就不会有自上而下的预期和假想的心理过程。 反之,在阅读中也很少有读者完全拘泥于文字本身,而不和自己的已有知识进行验证的。 因此,应该说自上而下模式和自下而上模式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结合才能体现理解中的互动进程。这里所谓的互动就是阅读图示和语言线索之间的互动,或者说是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传统的文学交际模式中由作者通过文本到读者的单向信息流动,就变成了作者和读者通过文本的双向互动过程。这两种活动相互协调,始终存在于阅读者和文本之间,存在于输入新信息和读者图式知识之间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暂不考虑作者这一因素,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可表现为: 文本读者。读者使用自上而下法处理不超出自身图式知识的输入信息,反之,对超出的信息则自动调用自下而上法。
相比较而言,这种综合模式更全面地概括了整个阅读过程中读者的理解活动。任何文本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先对文本的语言进行解码理解的基础上,但同时读者很少处于一个完全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是在阅读过程中经常对自己已有的知识内容,包括结构、文化、语言等图式不断地验证。以对侦探小说的理解为例,读者之所以被小说所吸引,是因为读者在利用自身心理图式对案件真相进行假想之后,其推想在阅读的验证或修正的过程中,不断因为被证实或被否定而欲罢不能。在最终结果被展现之前,读者始终有一种猜谜游戏的参与感,这种感觉使他们兴奋入迷,这正是这类小说的吸引力所在。如何使读者从始至终保持这种兴奋和参与感将是作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既然读者在互动认知模式中的侧重点不同,侦探小说作家对于读者认知心理的把握和引导也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点,下面以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这两位传统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家为例,具体分析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读解关系。
3、从柯南道尔到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作家对于读者认知心理的不同把握和引导
对于侦探小说中存在的两个过程,一个是案件从发生到结束的过程,一个是从侦探进行推理到得出结论的过程,作者多进行倒叙处理,即作者一般会先陈述案件结果,由侦探根据了解的情况进行推理,找出元凶,最后再由他解释推理过程。这种固定结构的特殊用意在于,利用语篇结构颠倒了案件推理中因与果的顺序,将推理过程最后推出,目的就是打乱读者的理解模式,获取最大的主导控制空间。可以说侦探小说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促使读者进行猜谜游戏。对于谜面文本的了解和读者的知识结构都是破解谜语的关键,但各个作者在文本中的侧重点不同,对读者在理解认知过程中的主动性所给予的空间也大有差异。有的对于读者图式外的信息不是按部就班地如实罗列,而是利用读者的知识“空位”,使读者没有多少余地进行自己的假想,与文本的印证过程也就降到最低点;有的则尽量把所有信息都向读者进行交代,使读者有更多机会进行自己的判断,和侦探一较高低。
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短篇小说来看,他始终遵循同一个模式:委托人来访说明自己的难题,福尔摩斯根据情况做出推理和判断,问题解决之后,再由福尔摩斯向次要人物和读者解释其推理过程。在人物塑造上,柯南道尔刻意树立福尔摩斯的绝对权威,目的就是要积压读者理解认知过程中的主观臆测的积极性。往往在一开始作者就会展现福尔摩斯的天才判断,例如从来访者的衣着、面貌上看出来人的来历等,读过《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的读者一定还记得, 福尔摩斯一见华生就指出“您到过阿富汗”,让华生和读者都惊讶不已。这种先声夺人的权威架式使得读者或者因为缺乏专业知识、或者因为华生对情况所做描述过于粗略等原因而只能静等福尔摩斯的高见。故事的讲述者(一般是华生)以及小说中其它人物的言谈举止都被用来烘托福尔摩斯的正确权威。例如在《波西米亚丑闻》(A Scandal in Bohemia)中,华生推论说委托人收到的书信上的水印是“制造商的名字”,福尔摩斯根据自己超常的专业知识,则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多数情况下,甚至苏格兰场的专业侦探在福尔摩斯面前也显得滑稽无能。例如在《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中,对于如何理解罪犯在墙上留下的“rache”的字样,福尔摩斯驳斥了官方侦探莱斯特雷德的论点,以可信的推理指出这是个德文单词,意为“复仇”。有时福尔摩斯甚至对于自己的结论并未提供解释,但相关人员却完全没有异议,这一切都是作者有意为福尔摩斯营造一种神圣的权威的气氛。
福尔摩斯的世界中,读者的理解过程更多的是遵循自下而上原则,绝对相信作者或侦探的权威,读者要做的更多的是读解文字本身的含义,了解情节发展,接受福尔摩斯的结论。文本本身给读者提供的想象空间也不多,多数要借助于福尔摩斯的解释,读者自己很难建立任何事先的假想。以理性为依据的福尔摩斯的观察永远是正确的,读者只是一个被动的感受者,他看到的是所谓科学的,冷静客观的演绎法。这是一个封闭的,自成一体的系统,从而免除了任何怀疑(张小简,1998)。他的推断被认为和事实真相完全一致,读者在他的阴影下难以获得发挥自己推断能力的自由空间。柯南道尔所期望的读者正如赛亚赛亚(Sciascia, 1983)所说的:
“…(侦探小说)好的读者是这样: 他们不把自己置于调查者的对面,他不打算提前解决问题,他不想猜答案…他知道, 答案总是存在的,在书的最后章节; 他还知道,自己的消遣只取决于一种条件――让大脑绝对的休息,信赖调查者。”
下面以《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为例,来看看柯南道尔是怎样在树立福尔摩斯权威的同时使读者完全信赖其判断的。小说一开始,委托人尚未出现,福尔摩斯就从送信人身份和委托信水印的判断上使华生“大为惊讶”,而且“更加钦佩了”。而在血案的现场勘探中,华生的描述只能让读者看到一部专业侦探机器的运转,却不能提供任何实际线索:
他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茫然地注视着地面,一会儿又凝视天空和对面的房子以及墙头上的木栅。他这样仔细地察看以后,就慢慢地走上小径,或者应该说,他是从路边的草地上走过去的,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小径的地面。他有两次停下脚步,有一次我看见他还露出笑容,并且听到他满意地欢呼了一声。
不管是否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发现蛛丝马迹,柯南道尔在这里都根本没有给读者任何进行推断的机会,在有意隐瞒侦探的发现的同时,柯南道尔还不失时机地用华生的想法再次提醒读者:
然而至今我还没有忘记,那次他如何出色地证明了他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因此我相信他定能看出许多我所瞧不见的东西。
对福尔摩斯超群能力的烘托与对破案线索的隐瞒在柯南道尔的作品中十分常见而且相互映衬,其目的是明显的:使得读者除了等待福尔摩斯的结论和解释之外,别无选择。 因此在柯南道尔的作品中,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认知关系呈现出以作者意图为主的特点:作者在创作福尔摩斯系列作品时,通过各种写作技巧(如树立权威侦探形象, 保留重要线索, 短篇叙述结构等)来把握和控制读者的理解认知过程和进度;而读者则是在对文本的读解过程中,主要通过自下而上法, 辅之以自上而下法来领会承认和接受作者的意图。
这种过程体现出在柯南道尔的小说中,对权威的绝对信赖和崇拜可以说贯通始终,读者的预先假想近乎于零,读解过程中感受的好奇大于悬念。因此柯南道尔最受推崇的福尔摩斯系列绝大多数都是短篇小说, 原因并非如Bernard Benstock (1992)所说的完全出于方便杂志连载的经济原因,事实上,这种短小精悍的结构更利于保持对读者的吸引力,不会因为篇幅过长而使读者失去好奇心或产生被牵着鼻子走的厌倦感。
同属传统侦探小说作家的克里斯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柯南道尔模式的影响,甚至在人物设置方面也常常为主要侦探配上一位华生式的陪衬人物,但她的小说篇幅更长,人物更多,关系更复杂,因此她对于读者认知过程的把握就必然和柯南道尔有所不同,要使读者在线路更长更复杂的迷宫中乐而忘返,必须激发读者的探询兴趣,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克里斯蒂在其自传中明确写道:“我笔下的侦探一定要和福尔摩斯有所不同。”她的主要侦探形象波罗是个清高自负的退休侦探,另一个马普洱小姐则是个说话尖刻、好奇心重的老处女。他们从外形到气质都不具备福尔摩斯那种一开始就让人绝对信服的、权威“侦探机器”的特质。 在塑造这两位侦探时,作者更强调他们平凡世俗的一面,侦探对于案件的了解也不一定比读者多。
为了鼓励读者,作者不仅着色于侦探自身条件的不足,例如年纪大,行动慢等,甚至时时坦率地表现侦探对案件的迷惑,如在《无人生还》(There Were None)中,在听取证词之后,波罗感叹道:“先生,我不是魔术师,跟你们一样,我也迷惑不解。这案子进展异乎寻常。”和福尔摩斯的敏锐、无所不知截然不同,波罗表现的更多的是坚忍不拔和谨慎细心。 同样在《无人生还》中, 波罗:“我不是说过吗,跟你们一样,我也是迷惑不解。但至少,我们可以着手解决难题了。我们可以按次序有条理地把现有的事实整理出来。”
在克里斯蒂的小说中,读者会惊喜地发现:不需要知道如何破解密码,不需要熟悉各种艰深的专业知识,只要通过对人性的了解和细心的观察,自己也有可能找到破案线索(至少开始他们会这么认为)。这样读者就会更有信心利用自己对于探案的固有知识对小说进行读解。由此看来,预测和验证成为阅读克里斯蒂小说时理解认知模式的重要成份。
克里斯蒂的多数作品充分体现了“公平游戏”(fair play)的规则,为读者提供案件几乎所有的背景,侦探在对线索的掌握上并不比读者占多少优势,读者与正确答案失之交臂常常是由自身的思维定式和对细节的忽略而造成的。为实现和强化这种“公平游戏”氛围,克里斯蒂在叙事结构上也力求变化,以求超越传统侦探小说的固定模式。 例如,侦探并不一定从一开始就进入场景,在小说《五只小猪》(Five Little Pigs)中,波罗调查的是一宗十六年前的命案,所有的线索在波罗对相关人员的质询中也同时摆到读者的面前;在著名的《罗杰疑案》中,故事的叙述者本身就是罪犯,所有人包括读者和侦探一开始都受到他的误导;有时小说中甚至没有侦探,读者有机会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自行对案件做出推断,例如《无人生还》(There Were None)中,读者身临其境般地旁观一幕幕场景,目睹人物一个个死去,最后阅读到作为死者之一的凶手留下的自述叙述事件过程,才使读者恍然大悟获悉谜底。
克里斯蒂通过人物塑造和结构变化,不断引导和激发读者认知模式中的推测假想意识,加强读者的参与感。虽然传统侦探小说的模式注定了克里斯蒂的侦探最终会获得胜利,但其权威性不会达到象福尔摩斯那样使人顶礼膜拜的程度,相反,克里斯蒂的侦探在外表、年龄、性别和身体状况等方面所表现的平凡和迟缓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读者的挑战欲望。比较而言,克里斯蒂的读者比较愿意和容易进行自己的假想,然后同新出现的情况以及侦探的提示相验证。在这种不断验证、修改、再验证的过程中读者和侦探一起完成对案件的探索。换句话说,对于克里斯蒂的小说,读者多采用的是互动综合模式,既欣赏文本又参与猜谜,但侧重于自上而下的验证模式,正是这种读者的参与感使克里斯蒂的长篇小说长盛不衰。
可以说,克里斯蒂最大的特色,在于她能收放自如地利用各种写作技巧(如普通侦探形象,多层次叙述手法,繁复的背景和篇章结构等)把握读者的认知心理,在于她既给读者创造假想的各种条件又在最后巧妙地推翻其假想的能力。 这种促进读者参与,但在最后解决方案上却出其不意的技巧,显得比柯南道尔略胜一筹,这也是她最能折服读者之处。
4、结论
以上分析分别反映出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中作者、文本和读者的认知互动关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由作者创作出来的文本被读者读解,文本在读者和作者之间起到桥梁和媒介的作用,最终体现的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通过文本对读者施加怎样的影响,而读者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在多大程度上复现作者的原意,这是研究认知互动过程的重点课题。
同时,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侦探小说作为情节艺术,也反映出作者在塑造人物、把握篇幅上的功力。柯南道尔以短小精悍的结构保持读者的好奇心,目的是要读者偏重于自下而上法通过理解文本来接受权威。他的小说体现了侦探小说的基本要素,确立了传统侦探小说的固定模式。而克里斯蒂则升华了侦探小说的精髓和娱乐功能,她更擅长利用普通人物、复杂情节和多变结构刺激读者的挑战欲,使读者以自上而下法在不断地推断和验证过程中享受积极参与所带来的成就感。可以说,对读者认知心理的不同把握和引导形成了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在人物刻画和结构功能上的差异,创造出读者认知心理、文本以及作者三方之间不同的互动关系。从柯南道尔到克里斯蒂,侦探文学不仅经历了文本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功能的加强,在理解认知领域也出现了不同的手法以体现不同的写作意图。这方面的研究将是通俗文学批评价值研究的突破,同时也为主流文学的写作与品评带来新的视角。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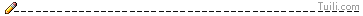
|
|
阿婆婆当年的离家出走之谜.....:)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侦探推理 > 欧美名家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侦探推理 > 欧美名家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5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5